名家作品欣赏孙文斌黑龙江密山山杏
山杏
□孙文斌
山杏刚走进那黑黢黢的房子里,就眼晕,被屋里臊哄哄的气味熏得直恶心。
井长老石指指头发零乱像堆烂草、衣裳脏得亮得泛光、脸上好似从生下就没洗过、萎缩在炕上的汉子说:“他就是田野。”山杏茫然地点点头,那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眼睛直勾勾地在山杏那丰满的身条儿上扫来扫去。
“瞅啥瞅,山杏就从今儿个起跟你过日子啦,野小子中意吗?”井长老石呲着大黄牙,唾沫星子乱迸。“中意,中意,爷们儿够意思。”那个叫田野的男人眉飞色舞地拍着手。
几个前来凑热闹的矿工油渍麻花地涌了进来,“哎呀呀,这田哥们儿也交了桃花运啦,”“头儿,啥时候给咱哥们儿踅摸一个。”他们油头滑脑地说着笑着。
“你们跑这儿来起啥哄,都他妈的给我滚远点。”井长老石瞪起牛眼珠子连吼带叫,那几个小子打打闹闹地走开了。
“野小子,我可把丑话说在前,你若是慢待了山杏,我他妈的扒了你的皮!”老石扭过脸很严肃地对田野说。“头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供还供不过来呢。”田野说。“这就好,这就好,山杏,这小子若是给你气受,找我老石,我决不轻收拾他。”山杏点点头。
老石又将两人教训开导了一番,就很欢畅地走了。
田野是工伤,三年前下井时不慎被一块滚下来的煤石砸坏了腰,左治右治就是不见强,腰以下一点知觉也没有。从此,田野就成了矿上填不满的坑,一年光药费花个上万元不说,还得用两个人昼夜侍候,这小子可有了胡作资本,三天两头就上井上、矿上胡作一把,医院不走,就是赖在矿部不动,稍不遂他心愿就捡起大砖头子把矿部大玻璃一顿乱砸,弄得矿上、井上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矿长一来火,把这个烂眼子事儿交给井长老石处理,老石跟田野谈了整整两天两夜,终于达成协议:矿上帮田野找个媳妇,每月矿上补助他五百元,顶这个媳妇的工资,另外每年给他医疗费五千元。老石把协议拿给矿长看,矿长很痛快:“中,这熊玩艺,这两年可把咱折腾赖了,这要求虽然过分点,就过分点吧。不过得公证一下,省得这小子翻脸不认人。”老石把协议公证后,就四下为田野撒眸媳妇。撒眸好长日子也没找到合适的主儿。一听田野是个瘫子,就连那些寡妇舍业的女人也直摇头。就在老石愁得直皱眉头时,那个山杏找上门来了。
老石听了山杏的名字心里就有些发酸,嗓子眼儿也像塞了团棉花,想了好一阵子才出了声:“姑娘,田野可是个瘫子,是个废人,你可寻思好。”
“我知道,别人已跟我说过了。”山杏垂着头,轻轻地说。
老石瞅了瞅盘儿条儿挺顺的山杏:“姑娘,多大了?”“二十整。”山杏又轻轻地答。
老石觉得有些话不好说,就把会计兼女工主任叫来了,在会计兼女工主任耳朵边嘀咕了半天,才走出屋,让她跟山杏说。会计兼女工主任跟山杏唠了好一阵才出来,对着直抽闷烟的老石喊:“这姑娘十有八九不怎么正常,任我千开导万解释,就是不开窍,愣不明白那回事。”
老石疑疑虑虑地跟山杏去了趟山里,想跟山杏的爹妈见见面,心里好托底。两人整整坐了一上午客车,又步行了三个多小时,才从密密匝匝的山林子缝中隐约看见一个小屯子,山杏说:“这就到了。”老石漫不经心地望了望七扭八歪的屯子,把目光投向沟塘子边开着一片粉白色花的树上,挺舒心地问:“山杏,那开花的树是啥树?”“是山杏。”老石又把目光投向山杏那张跟杏花般的粉白色的脸,就不知怎么产生了喜欢这个土里土气名字的感觉。
山杏的确是一个苦透腔的山杏,山杏家是外来户。山杏只知道老家紧靠黄河边,那年黄河水泛滥,把她家那几间低矮歪扭的小草房,连同几亩光种没收成的薄地冲个一干二净,爹就领着妈和她及两个弟弟一路讨要才来到这山旮旯里,以采药材采山货为生。山杏打小就跟爹妈钻林子、采蕨菜、采蘑菇、采木耳,反正林子里能卖钱的东西全都采。
山杏顶喜欢这沟塘子边那片山杏树,一开春,枝头树梢挂满着粉白色的鲜花,好漂亮。入了夏,山杏把结满山杏的山杏树摇个山响,成熟的山杏就像雨点般地往下掉,山杏用条苕一扫就是一筐,往家里大院上一倒晒上几日就能自动脱皮,脱皮之后再一个个地砸,捡出山杏仁,集多了爹就拿到中药店去卖,好贵好贵呀,山杏身上那个透着花蝴蝶的红毛衣就是用卖山杏钱买的。山杏好开心,别看山杏不能吃,但山杏仁却是宝贝,乍一吃苦涩涩的,越嚼越香甜,越嚼越有滋味儿。
山杏就觉得自己就是那山杏。一打眼看不出什么奇特的地方,可细细品尝才有味道。
山杏更恨那片山杏树,那片山杏树使他丢了女儿身,使她永远在人面前抬不起头。
那是在她十三岁那年夏天,山杏忘情地摇晃着成熟的山杏,山杏就像雨点般地劈里啪啦往下落。
“山杏,你可真胆肥呀,一个人钻林子,不怕叫狼叼走啦。”山杏的身后突然传来了声音,山杏吓得一激灵,扭头望去,竟是村长的儿子二歪,山杏厌烦而又畏惧地躲在杏树后边。
二歪顶不是物,整天除了吃喝就是嫖女人,村里的女人几乎叫他作践个遍,倚仗他老子是村长,胡作非为。
“别怕,别怕,我帮你捡”二歪嬉皮笑脸凑上去,“别过来,要不,我就不客气啦。”山杏举起那把镰刀。二歪色迷迷地在山杏身上扫视着,嘿嘿一笑:“娘的,大爷就喜欢你这样任性的小野篙子。”二歪把那个带把的烟屁股吐了出去,猛虎下山般地向山杏扑了过去,山杏死命地挣扎着,但怎能抵挡住二歪这个二十刚出头野兽般的欲火,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山杏就晕了过去……
“这个狗揍的二歪真不是东西,这几天我没轻收拾他,不过,不过,事已出了,泼出的水再也不能收回了,你们看这么办行不?我使使劲儿,托托人,帮你们把户落上,再给你家分点地,也算是对山杏的补偿吧。”村长叼着带把的烟,打着饱嗝,喷着酒气对山杏爹妈说。“村长,俺们不是要这些,只是想,山杏这孩子太可怜了,这么点儿就叫人作践了,往后可咋做人呀?”妈说不下去,就呜呜哭了起来,村长厌烦地皱了皱眉头:“别这么哭哭啼啼的,说个痛快话,这个办法到底行不行。”爹死劲儿地抽着旱烟卷,妈依然抽泣个不停。“嘁,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磨嘴皮子,是告是罚,我奉陪到底。”村长拾起那件挺有派头的皮大衣抬起屁股就要走,“别,村长,就按你说的办吧!”爹老泪纵横,艰难地说。
从那以后,山杏的心中就压了块石头,村里人都躲得她远远的,人们谣传得越来越花花,五花八门,有的说,这小野妞,真不规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竟去勾引村长的小子;有的骂,真他妈的不要脸,才十三就干那事。山杏就是在人们的唾骂和斥责声中长大的。
山里人兴早婚,山杏到婚嫁的时节,却无人问津。有人给她提亲,可相亲的男人一听山杏有那段丑事,都摇头离去,就连那些鼻斜嘴歪的汉子,也都没正眼瞅过山杏。山杏成了爹妈的一块心病。
老石钻进山杏低矮破烂的家,山杏妈正有一搭无一搭地砸着山杏核,山杏爹胡乱地用围裙擦了下炕说:“坐吧。”老石就坐了下来,“田野那小子是个瘫子,工伤,山杏嫁给他可要苦了一辈子呀。”老石一五一十地说。
“哼,这个俺们早知道,没挑,只要山杏能嫁人,饿不着,俺们就知足了。”山杏爹淡淡地说。
“那小子脾气挺操蛋,动不动就犯驴。”老石又说。
“咳,一个瘫子再能作还能作到哪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俺们山杏就是这样的苦命人,认了。”山杏妈停下手中的活计,忧伤地说。
老石眼圈儿有些发红,再就一句话没说出来。
“大叔,你咋还不放心?”山杏眼巴巴地望着老石。
“山杏,别叫我大叔,就叫我大哥吧,我今年刚三十。”老石说。
山杏说:“这可不行,你是田野的头儿,比村长还有权。”
老石临走时说:“大叔,大婶,山杏就交给我了,有我在就绝不能让山杏受屈,我就是她的亲哥。”山杏爹妈感激不尽,说了好多直让老石落泪的话。
老石在山杏家就着大咸菜嚼了两个大馒头就红肿着眼睛带着山杏走了。
路过那片山杏树林子,老石止住脚,呆呆地瞅着那粉里透白的山杏花发愣,山杏不解地问:“你瞅啥呐?”老石说:“我瞅瞅这山杏花到底啥模样。”
山杏把田野住的两间小里屋收拾个透亮,蹲在大洗衣盆跟前,一洗就是一整天,把那些臊被子、脏衣裳全都洗个干干净净。山杏把衣裳挂在外面晒上后,对田野说:“田哥,咱是不是把房子刷刷,也像个过日子的样儿。”田野说:“中,你推我到井口一趟,我找老石去,让他派人帮着收拾。”山杏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麻烦人家,我自己就能干。”
山杏刷房子时,田野那些狗哥们儿来了不少,这个说帮着买酒,那个说帮着砍肉,眨眼工夫就跑个精光,田野好得意:“山杏,咱哥们儿人缘可以吧!这帮伙计还能惦记我。”山杏扬起脸笑笑,惟独那个双利没走,望了望忙得不可开交的山杏,就说:“嫂子,我帮你刷吧!”也不管山杏同不同意就夺过了绑着滚刷子的长杆子,双利个头高挑,那刷墙的姿势也特耐人看,像是在练健美,肌肉一疙瘩一块,让山杏看了好舒畅。山杏知道,双利是田野的老铁,也是孤儿,没家没业,在矿里食堂上灶,山杏没来时,双利照顾田野一年多,对田野忠心耿耿。“双利,今年多大了?”山杏问,“二十三。”“哎哟,比我还大三岁呢。”“那,那你得管我叫哥哥啦。”“不行,萝卜不大辈在那,冲你田哥那边得喊嫂子。”“各论各叫吧,当我田哥面喊你嫂子,没人时叫你妹子,行吗?”山杏没答,脸红红的。“双利,有对象了吗?”双利摇摇头:“又穷又熊的,谁跟哪?”“哎,俺们村可有不少好姑娘,我给你介绍一个咋样?”“可以,不过得像你那样漂亮、水灵。”双利嘻嘻一笑,“你个坏小子,真讨厌!”山杏飞红着脸,这些年她第一次听到别人夸她漂亮夸她俊美,心里就有一丝的甜美。
等山杏和双利把房子刷亮了,那帮操办着吃喝的哥们儿也个个满载而归。井长老石也来了,进屋就喊:“嗨,旧貌换新颜啦,不错,不错,像个过日子样儿。”大伙就你一句我一句把山杏好个飘扬,老石也沾沾自喜:“我老石眼力还可以吧!”大伙就恭维着老石。
“你们全借了我山杏妹子的光,若不是看她的面,我他妈非整出你们的稀屎。”那帮狗哥们儿直呼老石万岁,就手忙脚乱打罐头、切肉、摆桌,还是老规矩,每人一瓶“北大荒”,对瓶吹。山杏听田野说,矿上就这规矩,十个煤黑子九个骚,一个不骚大酒包,个顶个能吃能喝,不吃不喝不玩不乐省下干啥,干着阴间活,吃着阳间饭,有了今天说不上没有明天,矿工们个个想得开。
吃饱喝足了,就是胡吹神侃,说得好花花,说得山杏直脸红,说的内容大都跟女人有关,大都是干那事,山杏就悄悄地躲在里头的小屋里。
有个小子说话时舌头都大了:“田哥们儿,别他妈的好吃不撂筷,隔三差五也得让咱哥们儿尝尝鲜,开开荤。”几个小子也随帮唱影:“就是,就是,咱哥们亏待不了你,有福同享嘛。”
山杏隐约知道,矿上的人对男女之间的事儿看得很轻很淡,只要两个人愿意,别人不追究,即使是两口子知道自己的媳妇或男人在外边跟别人扯也不放在心上,两块石头夹块肉的煤黑子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钱今朝乐,不管今后死与活。山杏听着那帮男人不堪人耳的话,大脑就变得浑糨糨的就想起了那片可怕的山杏林,那白花花的山杏花就纷纷地在她眼前飘落。
突然,她听到了田野的干嚎声,干嚎得好惨好惨,紧接着是老石大发雷霆的怒吼声:“我操你们八辈祖宗,丑话说在前,谁要是打山杏的主意,我老石跟他玩儿命。”
山杏时常在阳光足的好天里,用轮椅推着田野出来放风。山杏觉得矿上哪都好,就是不如山里的空气好,风景美,街上的人虽多,挺热闹,但乱哄哄的,把脑瓜子吵得生疼。山杏就时常把田野推到离矿上不远的小山坡上,山坡上长着一片片玻璃棵子和荒草,也夹杂着一些各式各样的花儿,山杏把轮椅停放好,就踏进草丛里,尽情地采着黄花、喇叭花,什么时候采足了,什么时候才回来。
“山杏,你在大山旮旯里呆了那么多年还没呆够?”
“嗯,永远也呆不够,那地方可比咱这有意思多了,不像咱矿上,一出屋就是雾气腾腾的,走一圈儿回来一脸煤灰子,满身漆黑。”
山杏来了精神,就好得意地说:“俺们那地方,别看穷,但真的好漂亮,一开春就有映山红,紧接着就有黄花、马蹄莲、大芍药,那芍药一开可好看了,我就专采那些还没开的花骨朵儿用瓶子装上放在窗台,没过几日,就开了,开得满屋里都是清香。大冬天里也好有意思,大山小岭叫大雪一盖,狍子、野鸡就往屯子里跑,我们就撵啊撵,有时真能逮着跑不动的动物呢。”
田野听着听着直流口水,听着听着便又哀叹道:“唉,我要是不残废该多好哇!也到你家里那地得好好逛逛。”一句话打消了山杏的情绪。山杏也找不到合适的话可说,山杏就心里空落落地推着轮椅往回走。
山杏就再也不主动推着田野往山边走,大都去那些热热闹闹的街里,进了街里,田野的话就多了,净讲些山杏从未听说过的事儿。
“知道吗?俺们矿是小日本子侵占时建的,那边是过去的澡池子,这边是过去的妓院,就是专养挣男人钱的女人,现在改成宾馆了,也养了一些专挣俺们煤黑子钱的女人。”
山杏听了直叫:“这些女人真太那个,干啥不行,偏干这个。”
田野就有些得意:“嘁,你懂个啥?这叫无烟工业。”
山杏不敢多问,就替那些女人害羞。
到了夜里,山杏最难熬,田野动不动就发火,不是摔盆就是摔碗。山杏知道,田野心烦苦恼,他已不是完整的男人。看到田野夜里的样,山杏就好难受,好后悔,明知嫁给田野是往火坑里跳,可自己却心甘情愿往里跳,但一看到田野耍过疯后,又是疼爱又是内疚地说:“山杏,实在太委屈你了,你若是心里难受,过够了,想离开就离开吧!”山杏心里好矛盾,不知所措。
井长老石常来瞅瞅,问这问那,动不动就把田野教训一番,田野也变得好乖巧,然后再问山杏田野待她咋样,有不地道的地方尽管吱声,由他收拾,山杏总是把头摇个不停,忙说没有没有,他待我挺好。老石就露出难得的笑容,说:“这就好,这就好。”
田野那帮哥们儿也照常来赌来喝,赌完了就喝,喝完了就扯,一直扯到人困马乏时才离去。山杏就成了这伙人的义务服务员,烧水,做饭,忙个不停。
山杏几次想对田野说,别这样了,这哪是正经人过的日子?可一想,田野也够可怜、苦恼的,就这么一点点兴趣再给他剥夺了,实在不忍心。
田野的这帮哥们儿中,惟独双利特别,从不大吃二喝,犯赌,顶到头凑凑热闹,双利天天来,给山杏挑水,山杏和田野住的是老式旧房,没有自来水,得到一百多米远的供水点挑水吃,自打田野瘫了后,挑水的活儿就成了双利的专利。双利进屋后,不多说话,挑完水说上一句:“大哥、嫂子还有什么活儿?”得到明确答复后,就走。连口水也不喝。
老石阴沉个脸来到山杏家里,狠命地吸了两颗烟后,才艰难地张开嘴:“兄弟,我对不住你,更对不住山杏。”还没说完,眼圈儿就红了。
原来矿上亏损严重,把井口全部拍卖、租赁给个人或单位,对于田野这样的公伤也降低了标准,能够给发点生活费就算烧高香了,其他甭想。就连老石这样的井长也只得自找出路讨米吃。
老石觉得对不住田野,这小子是在他当井长时造残废的,更对不住山杏,田野那点救济金连吃也供不上。
田野听后聋拉下脑袋,不像往常那么不对他脾气就吼就骂,山杏更是没了章程。
田野那些狐朋狗友也极少在田野家凑群了,大都在劳务市场上站大岗,拎大板锹、卖零工。
矿里每月只给田野一百多元救济金,其他什么也没有,山杏和田野的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山杏推着田野找了两回矿里,矿上都卖给外人了,谁还管这些烂眼子事儿,山杏和田野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山杏寻思了一阵说:“田哥,咱们干脆回俺家那个地方,我采山货、采山菜、采山杏卖,咱们日子也有个着落。”
田野无力地摇摇头:“这样,太委屈了你,山杏,你跟田哥过得不憋屈慌吗?”一句话弄得山杏泪水涟涟,就掩着脸向家里跑去。
夜里,山杏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直烙饼,田野说你是不是累了,要不,就别干了。山杏说,那可不成,双利的店光他自己打不开点,山杏就盼着早点天亮,越盼时间过得越慢。山杏就想到在家里那些的时光,钻山林子,采山货,春天的时候,山杏头上挂着粉白色的山杏花,满山遍野地采着蕨菜。她美美地想,等出嫁时,就选在杏花开放的时候,头上挂满杏花,接亲的车也挂上山杏花……
可就这点点的愿望也没实现,山杏的泪就情不自禁地淌,把枕头洇湿了一大片。
起了床,山杏就觉得头昏脑涨,六神无主的。她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慌恐。
山杏对双利说,俺们那山沟里真的可好了,那小河水清得能看见底,鱼儿游来游去看个真亮,我们常用土篮子捞,一捞一个准,用不上半个钟头,就能捞一大海碗,老头鱼、泥鳅、鲫鱼、柳根子、白漂子,什么鱼都有,若是赶上雨水大的时候,好几斤的大鲤鱼都能逮着。
山杏说,山里可不像咱矿上这么费钱,菜自己种,粮自己种,柴自己打,房自己盖,不像咱这儿,离开钱就玩儿不转,上趟厕所还得花上一毛钱,邻居处得也不像这么掰生,常端个饭碗挨家串,边吃边唠,可有意思了。
山杏越说话越多,不光把双利吸引住了,就连那帮吃饭的客人也立起耳朵听。山杏一直说到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天已煞了黑。
山杏止不住嘴,忙数钱,将元、角、分分类归整好,就在山杏将点好的钱交给双利的一刹那,双利火山爆发似的扑向山杏,山杏一阵眩晕,浑身灼热,顿时涌上难以言状的愉快……
“山杏,跟我走吧!就凭咱俩这般认干劲儿,到哪都饿不着。”双利亲吻着山杏。
山杏泪水涌出,摇摇头:“不行,那田哥咋办?”双利把山杏紧紧拥在怀里:“你真好。”
山杏泪流不止。
“你哭啥?不高兴吗?不喜欢我吗?”
“不,我怕,我怕田哥知道我这样他会寻死。”
“那,那,干脆跟他摊牌,咱俩成亲后养着他。”
“行吗?”
“我看行。”
山杏喜忧交加地回到家,心里就跳个不停,惟恐让田野看出破绽,草草地洗把脸就钻进被窝把头蒙上。“山杏,你累啦?”“嗯。”“山杏,你不舒服?”“头有点沉。”“那我给你揉揉。”“不用,不用。”山杏忙拦着。
山杏怎么也睡不着,闭上眼,就回到了和双利的那一幕,那是让山杏终生难忘的一幕,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做女人的滋味,第一次尝到了与心爱的男人欢愉的感觉……
山杏又仿佛回到了那个山旮旯里,满山遍野依然开着各式各样的鲜花,山杏总也采不够,总也采不完,等采累了就倚靠在那片山杏树下乘凉,飕飕的小风不急不缓,好舒坦,消了汗,就到不远的小溪里戏水,尽情地抓着各种各样的小鱼儿……
山杏喜气洋洋地头上插满杏花,穿着红衣裳出嫁了,双利更是欢天喜地,一脸的幸福,田野也好兴奋,说,山杏,你快跟双利生个小山杏,我好有营生干,整天哄着,你们出去支摊。井长老石笑着说,这多好,这多好。大嘴快咧到耳根子了。
山杏从睡梦中醒来天已大亮,揉揉惺松的眼睛,忙对田野喊:“哎呀,都过点了,我得赶快去。”说着匆匆洗把脸就向双利的小吃铺疾步走去。
======================
孙文斌,男,年出生,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全国四十余家文学期刊发表二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获文学创作奖,著有四部中短篇小说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在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供职。
声明:原创作者作品抄袭剽窃责任自负
主编:瑞雪制作:腊梅
转载请注明:http://www.hdnzi.com/wahl/632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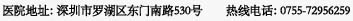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