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经典黄昏里的男孩
我们被山庙村人抓住的时候,太阳落下去了。太阳就像趁机逃走的人,只顾自己逃,丢下我们被押往山庙村。一路上天色越来越暗,暮霭越来越重,一旦脱离抓捕我们的人的火把照亮,人就会被黑暗吞没,或者被他们手中的猎枪打死。我们都不敢逃,又不甘被抓,走在最前面的阿庆扔下肩上的树,跪下来求饶,立刻挨了重重的一脚。“背上树走!”“我想回家!”“回家?还想回家?走不走?!”那些人踢他,用树枝抽他。火光的晃动,疼痛的叫唤,还有黑夜降临以后充满肃静的气氛,让人感到无助,只能顺从。虽然说,我们村与山庙村只隔着一座山岭,我们被抓的地方离山庙村更近,由于看不清路,肩上还要背着偷来的树,一路上不断有人跌倒,哭泣。我也早已精疲力竭,肩膀被粗糙的树干磨破,痛如蛇咬,走下坡时两条腿直打晃,可我不敢哭,只有眼泪不住地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希望早点儿到达山庙村,早点儿把树从肩上扔掉,倒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也不知走了多久,摔了多少跤,终于在山脚下稻田的尽头出现了灯光,那灯光即刻让人忘记了危险的处境,仿佛马上就要到家了似的。可是把我们关起来的地方,却是黑乎乎的,没有灯,也没有吃的。那是一座阴森腐朽的庙宇。一个声音冲我们吼道:“三天内,你们的爹娘不来山庙村交清每人二百元罚款,就把你们几个活活绞死在这里!”谁家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呢?一定是吓唬我们的。此时我们更关心的是晚饭在哪儿吃,又怎么可能在这阴冷恐怖的破庙里捱过一夜?我们当中年龄最长的阿东,拍打快要合上的庙门,要求他们送来热饭和棉被,并且喊道:“你们村的偷树贼被我们村抓住后,可是住在‘树干部’家中管吃管住,顿顿吃好的!”
“什么,放你娘的狗屁!以为凭一张嘴就能颠倒黑白吗?”说话人晃动火把,仿佛要把它砸在阿东的头上,阿东跳开了,再回头却发现那人在解开自己的上衣,只见通红火光中裸露的胸脯上伤痕遍布,就像一堵被撕过的、残留着红色纸片的墙。原来,他是被我们村抓住过的偷树贼之一。“看看吧,这刺棘抽的疤痕!十里八村没有比吴村人下手更黑!”那人悲愤地说着,挥舞火把,突然冲上一步,揪住阿东的衣领:“哼,还没好好收拾你们呢!他娘的,做贼还想吃饭睡觉?抬一口棺材来睡不睡……哈哈哈哈!”
阿东的喉咙发出窒息的声音,我们却不敢上前去救他,因为那个人的表情和笑声太可怕了。好在他的手不久就松开了,阿东蹲在地上哇哇空呕的时候,庙堂突然变黑,大门合上了。我们就像坠进恐怖的深渊,有人带头哭了几声,接着大伙儿哭成了一片……
我们一共六个人。阿东是我的堂哥,这次到岭背上偷树就是他叫上我的。其人是阿庆、阿军、阿宏和阿平。我们当中只有阿东和阿庆跟着大人偷过树,其余都是第一次偷,谁会想到第一次就会被抓住呢?关于偷树贼的下场,我是亲眼目睹过的。记得有一年,一个偷树贼被吴村的“树干部”抓获了,从山上押回来的路上,“树干部”不但让他背着沉重的树,还把他的草鞋扔掉了,让他赤脚从河滩上走过。我们一群小孩正在潭中洗澡,见偷树贼在卵石上歪歪斜斜,难以负重。这时“树干部”就用手中的荆棘条抽他的小腿肚,每抽一下,那人就哀叫着跳一下,那东倒西歪的样子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当偷树贼被逼着蹚河的时候,湍急的水流割着伤口,他浑身战抖起来,肩上的树“咚”的一声掉进了水中……
“哈哈哈哈!”每次抓到偷树贼的日子,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之一。这样的日子带给我们许多快乐。我们可以尽情地向他投掷石块,吐唾沫,跟着游街的队伍大声呼喊,嬉闹。当游街完毕,我们还不肯离去,就像蹲在屠宰场四周的狗。一个又一个偷树贼,像一个又一个被俘的敌军,绑在大会堂的某一根柱子上,胸前挂着一块写着“贼”字的木牌,往往脑袋低垂,面容憔悴。
只有一次例外,有一个偷树贼被抓之后始终在笑。不论问他什么,他只会用“嘿嘿”作答。原来他是一个傻子。他关在大会堂里许多天,竟然没有人来交罚款。“树干部”家刚好造房子,就逼迫他去服劳役,挑土,挑石头,砍树,做农活。他想逃,又被抓回来,用棍棒、皮鞭、锁链教训他。后来他死了,死于一户人家的丧事上。因为他已成了全村人的牛马,那户人家借他去挑砌坟墓的条石,他可能很久没有吃饱饭,以致于在丧饭上吃得过饱,没完没了地打着蛙鸣一样的饱嗝,最后一个饱嗝打得有些奇怪,有人走过去一看,见他张着嘴瞪着眼,撑死了。
傻子死后,他的家人这才从山庙村赶来了,他们在村长家门口呼天抢地,要求赔偿一条人命的钱。不知事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只记得那些人抬着傻子的尸体离开前,针对我们村所有人发出警告:“等着,事情不会就此了结的,不管哪一天,不管抓到你们当中的谁,见一个打一个!除非,不踏上山庙村一步!”
迷迷糊糊中庙门打开了,天还未亮透,湿冷的空气还有咚咚的脚步声涌了进来。昨夜揪住阿东衣领的那个人带着一个满脸刀疤的人,进来后就把我们踢到一边站着。刀疤男人问:“就是这几个兔崽子?从岭背上抓来的?”“嗯。偷咱村的集体林。”刀疤男人哼一声,把目光转向阿庆,问:“你小子昨天偷树了?”阿庆红着脸,缩着脑袋。“问你呢!”那人咆哮道。阿庆很不情愿地点点头。一个巴掌打在他脸上:“记住了小子,以后莫做贼,做贼必被抓!哈哈哈哈!”
打完阿庆,又问阿东:“你小子也偷树了?”阿东说:“我们的树不是偷的!”“说什么?”“岭背上的树,两个村都有份。”阿东因为这句话,被那人连着扇了好几个嘴巴,牙龈血都流出来了。那人气咻咻地说:“既然岭背上的树都有份,你们村为什么要把我们村的人抓走?”那人在“你说你说”的咆哮中,一个轮一个地指着我们问。当他的手指头指向我,我吓得发抖,我认出他就是那个曾经被“树干部”扔掉草鞋,赤脚走过河滩的人。
“待一会儿,就挂上牌子去游街!”那人说着,就找来绳子和纸板,在我们的脖子上套一个“贼”字。然后命令我们向村中央走去。此时山庙村人都起来了,听说抓到偷树贼,都端着碗走出家门。他们用敌意的眼神盯住我们。一帮孩子高呼着:“偷树贼,偷树贼!打死偷树贼!”他们手拿小石子、土块、杂物,朝我们投掷。
过度的紧张恐惧,疲惫与饥饿,还有被当作贼游街的耻辱感,使我虚汗淋漓,两眼发晕。但我坚持着,不去看路边的人,不去理会身后追着叫的人和狗。但那些人影,叫声,敌视的眼神,层层包围着我……
游街游了一个上午,回到庙中时,我们满脸汗渍、泪痕,人仿佛瘦了一圈。中午,又有人哭泣了。此时哭泣是因为饥饿。阿庆说他要昏过去了。阿军说他的肚子里只剩下蛔虫。我也感到好乏好饿,悄悄问一言不发的阿东,我们什么时候才有饭吃?阿东想说什么,喉头一吞咽,眼泪就下来了:“说不定下午,我们村就会派人来接我们回去了!”阿东的话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想象下午村长会带领各自的家长来赎我们回家。但是事实证明,我们过于天真了。
下午的时候,阿平虽然被他的“建业叔”接走了。但“建业叔”接走他时,对剩余五个人连瞧都不瞧。反而山庙村人拦住他问:“那几个你不管吗?”他说:“我只管我自己的孩子!”事实上,阿平不能算他的孩子,他只是阿平他娘的老相好罢了。他是一个走村串寨的木匠,多年来一直“赖”在阿平家,与阿平真正的爸爸同时拥有一个风骚的女人:阿平他娘。这样一女二夫的事,在我们村不算稀奇,却也不光彩。大人小孩常常辱骂他们一家。所以,他才对我们如此不管不问的吧?
但不管怎样,他在离开山庙村之前,终究做了一件好事。他带阿平去了一户人家,并且说:“姐,几个吴村人关在山庙村,你不知道吗?”“怎么不知道,早上背着树游街了。”“他们一天没吃饭。我虽不是吴村人,但以后还要在吴村住下去,如果你希望我在吴村过得好,就给那几个孩子做一顿饭送过去。”那女人心不甘情不愿的,把一筐红薯连泥带皮煮了,在黄昏来临之前送到庙里。虽然说那女人长得丑,对我们的态度近乎施舍,但她煮的红薯实在太好吃了,我们根本无暇剥皮,连吞带咽……以至于阿庆因为吃得过快,在吃下第三个红薯时噎住了。当他把食物从呼吸道里抠出来,就像中毒的牛犊一样呕吐不止,那样子把我们吓坏了。
那女人见了,大概动了恻隐之心,跑过去对几个看守说了几句。那些人恶狠狠地回答她:“饿死、撑死、绞死,都是死!反正都得死!你不要多管闲事!”然后,又对我们吼道:“还有两天时间!如果你们的爹娘不来交罚款,非把你们一个一个勒死在房梁上!”
晚上却着实热闹了一阵子。本来山庙坐落在村外,夜幕降临之时,除了溪流、鸟叫、虫鸣,寂寂无声,但是由于我们的存在,这里始终有人来来往往。有的问逃走了吗?有的拿手电筒往庙堂内照。刺眼的光束粗鲁地打在我们的脸上,那感觉就像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扇耳光。有一个人甚至把一条狗放了进来。那狗冲到我们跟前龇牙咧嘴地叫着,仿佛要咬断我们的腿和胳膊……
然而狗并不是最可怕的动物,就在孩子们带狗离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蓬头散发的人哇哇哭着,从外面冲了进来。那是一个癫狂的黑影,张牙舞爪着扑向我们。她的到来再次引起山庙村人的围观,顿时手电筒的光亮重新聚集。“傻婆,你要干什么?”“我要杀死吴村人!”“你走开!他们会受到惩罚的。”“我要替我儿报仇呀……”一阵如同争执的劝解之后,那人才被大伙强行拖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她是曾经死在吴村的那个傻瓜的母亲。
“他们一家都在山上烧木炭,刚刚知道抓住偷树贼的事吧?”
“她那几个儿子呢?啥时候赶回来就麻烦了。”
“据说到湖镇卖木炭了。”
“这几个孩子怪可怜的,趁早放了吧。”
“放屁!当初你没有被抓走过不是?如果抓你去吴村尝尝被挨打的滋味,就不会这么说了。血债拿血来还!”
“那还不是你们几个把吴村人先抓回来拷打的?”
山庙外全是人,叽叽喳喳着,就像在点评刚刚结束的一出戏剧。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及时来山庙村交出罚款,只有死路一条:不是饿死就是冻死,或者被打死绞死。这是一个让人恐怖的村庄,这个村庄虽然与吴村只隔着一条山岭,但是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当我们被迫背着偷来的树踏上这个村庄,就意味着不会轻易放走了。想到那凶险叵测的下场,我们沉默不语,想着心思。
我想的是我的母亲,她走在灰白的道路上,四处借钱。村子里有可能借钱给她的,也就那么三五户人家。每次母亲去借钱,总爱带上我。有我的存在,仿佛给了她许多开口的勇气。只是自从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借的钱总是不能按时还上,那些人家见了母亲变得冷淡。有一户人家甚至让女儿撵我们走,骂我们“讨债鬼”。想到母亲每次从那些人家借到十块二十块钱出来,想哭又忍住的样子,我的眼睛湿了。
我跟阿东上山偷树,母亲是反对的。“再苦再穷,也不能去偷树,那也是做贼啊!”她这样说。可是,每一棵树都能卖钱,村里的大人小孩也都在偷。我也想给家里攒一点钱啊!尤其看到隔壁的阿东跟着大人去偷树,把偷来的树剥皮后晾晒在老屋的天井里,树身光滑纤长白皙,看着诱人。加上他每次卖了树就去买肉吃,闻着从他家厨房飘出的青椒炒肉的香气,我直流口水。我问阿东,偷树算不算做贼?阿东说,偷自己村里人的树是做贼,抓住后很丢人,偷外村人的树不算做贼,那是你的本事。我问为什么。他说:“能偷回外村人的树,村里人谁也管不着,而且需要胆量才行,村里人当然佩服你。”
末了,阿东劝我:“我叔常年生病,不是缺钱买药吗?你也跟我一起去偷树吧!我带你去岭背,树由我来帮你砍,难走的路由我来帮你背,怎么样?”我说:“我怕被抓住。”阿东说:“抓个屁。我们只在两村交界的山上砍树,砍树时你负责放哨,他们一来,就丢下树跑。他们不敢追到山界的这边来。”我的心蠢蠢欲动了。第二天,我瞒着父母,跟阿东走了。
逃!一定要逃走!也不知是巧合还是人与人的意识产生了交织,就在我黯然神伤,为母亲如何能借到二百元而担忧的时候,恰恰听到阿东在说逃走的事。因为担心被庙外的看守听到,他们把声音压得很低:“我们从屋顶逃出去。”“屋顶这么高,怎么爬上去呢?”“没看见这些柱子吗?”“被他们发现怎么办?”“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胆小鬼,跟着我爬就是!”
阿东说干就干,就像一只猿猴爬上柱子。那柱子有脸盆一般粗,笔直地伸向穹顶。上面阴森森的,就像倒悬的黑洞。阿东爬到柱子顶端,在上面窸窸窣窣地忙着什么,过一会儿又气喘吁吁地下来了。他说屋顶的椽木很结实,覆盖的瓦片是琉璃瓦,弄不动,人又没地方站,在上面待一会儿就没力气了。我们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阿东发现了出口似的,兴奋地说:“对了,可以从神像的头顶逃出去。”话音刚落,他就选择了另一根柱子。那根柱子紧挨着神像。所以他爬上去之后,可以将一只脚踩在神像的头上,这样他就能使上劲了。
不多时,屋顶的椽子就被阿东搬开了一角,瞬时有一束光从屋顶上泻下来。那是月光,但是很亮。“喂,都愣着干什么?一个一个往上爬呀!”阿东在上面喊。可是,下面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既担心门外的看守会推门进来,又担心爬到高处会摔下来。大伙都等着别人先爬上去,以便心理更有准备。但是这种想法随即变成了胆怯,有人轻声嘀咕:“说不定明天我爸就来赎我回去了。”“半路上也会被山庙村人追上的。”听了这些,本想跟随阿东逃走的我也有些犹豫了。
阿东在高处等得不耐烦,自己先从刚挪开的豁口往外爬。爬的过程中,那破旧的屋顶嘎嘎作响,杂碎不断地掉下来,因为声响有些大,我们屏住了呼吸。“喂!谁先上来?琉璃瓦踩不碎的……”阿东从那个豁口探进头来,压低声音喊,“不用怕,快上来吧!爬上来以后,我拉你们出来!快点呀!”
“我们害怕……”阿宏低声说。
“害怕个屁!再不上来,别怪我先走一步了!”
“等等,我上来!”阿庆迟疑着,抱住柱子,往上爬,但爬得很吃力。当爬到与神像齐高的地方,他要让一只脚踩在神像的头顶上,试了几次都不敢踩。于是又降到了地面上。
“该死,你怎么又下去了?”阿东在屋顶骂。
“那神像,那神像他……”阿庆结结巴巴。
“怎么啦?”
“他瞪我!”
“放屁!”
“没骗你,他是活的!不信你们看去。”
阿庆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了害怕。的确,豁口之下,银色的月光刚好照在脏兮兮的神像上,原本糊在神像头上的黄泥巴被阿东踩过,已经掉下来了。那神像的脸部尽管看不清,但是裸露的眼睛干干净净,瞪得老大,在斑斑驳驳的缝隙间睁着,仿佛在瞪着我们!我打了一个寒战。
“真是一群废物,连这个也怕,什么神像,还不是泥巴做的?!”阿东有些急躁了,叫起了我的名字:“阿昆,你先上来,我带着你逃!”可是,我跟他们一样不敢爬,但阿东是我的堂哥,他平时对我很好,又怎么拒绝呢。我硬着头皮抱住柱子,柱子又粗又滑,加上心里害怕,爬到一半就手脚发软了,终于爬到与神像齐高的地方,一抬头,看到神像依然双眼怒睁,我吓得想后退,松开了手。
那高度起码有六米,我在下坠的过程中拼命地想抓住什么,结果抓住的只有自己的尖叫。当尖叫声被“咚”的一声终止,我的身体随即被剧烈的疼痛俘获。这时庙门打开了,两根棍子一样的光柱穿透了我。“谁啊?干什么?!”两个看守看见摔在地上的我,又看见出现在屋顶上的豁口、被踩踏的神像,气得拿手电筒打我们。我因为站立不起蜷缩在地,他们就抬脚踢。
“他妈的吴村猴,贼骨头,想逃?!——把你们的脚筋都砍断,看你们还敢不敢逃!”我的眼睛被手电筒照住了,睁不开。但是我的耳朵能听见。我听见另外一个看守已经跑到庙外,去追赶逃掉的阿东了。我听见到处是狗的狂吠声,人的呐喊声,忽远忽近。
阿东逃跑后,留下我们几个绑在山庙里。此时天还未亮,山庙村人还没有重新汇聚到庙里来。可怕的寂静好比被蛇咬后,疼痛暂时消失,毒性尚未发作,或者出现了麻木。现在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了。谁知道他们何时到来呢?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下沉,我们盼着太阳升起,父母会随同阳光到来。与此同时,又担心随同阳光到来的是更严厉的惩罚。我们清楚,阿东的逃跑已经激怒山庙村人。他们将我们像粽子一样绑在一起,就是要好好折磨我们……我想起一脸刀疤的人说过,如果我们的爹娘不来交罚款,就把我们一个个勒死在房梁上。还有人说过“血债拿血来还”。想着想着,鼻子就酸了。
要是当初听妈妈的话,或者在偷树时早点儿发现包抄我们的人,甚至在爬柱子时不要摔下来,都不会面临现在的困境。可是当初我不认为偷树是做贼,偷树时我负责放哨,但毕竟是第一次放哨,紧张得要命。当我爬上直冲云霄的大树,听见山顶的风在树杈上发出嗥呼的声音,枝叶摇晃,脚下悬空,还有一种油黑色的蚂蚁在树干上乱爬,我才知道在大树上放哨的感受,与《鸡毛信》里站在大树下放哨的海娃,情形完全不同。海娃俯瞰的是光秃秃的山冈,而我看到的是郁郁葱葱的林海,满眼树冠,看不见炮楼,连一块裸露的岩石都看不见。而且山庙村人是从深涧旁的灌木丛中爬上山的,我却死死盯在筑有山路的山梁上。当他们出现时已堵住我们的退路。他们以追捕野兽的方法追捕我们,我们就像机敏的野兽于丛林间逃遁。我却逃进了他们的圈套。阿东本来是可以逃掉的,见我被抓只好主动回来了。因为缺了他的带领,其他人也纷纷落网。
现在庙里就剩四个人了。他们是阿庆、阿军、阿宏和我。现在就更难逃掉了。当然谁也不敢再逃。再加上捆绑在一起,无法卧倒休息,困倦和饥饿转土重来,身体的不适乃至疼痛,加剧了无望的情绪。不知什么时候,我听见了自己的哭声。可是那个哭泣的身体是阿军的。这个与我同龄的伙伴,他是村里哑巴的儿子,他从来不哭,他爹把他吊起来毒打也不哭。这次被抓,他一直像木头一样无声无息,现在我哭了,一吸一顿、呼吸急促、抽噎不止的,却是他紧挨着我的身体。
一种水要沸腾一样的悲情,很快在庙堂里膨胀开了。阿宏的哭声响起来以后,很快压过了我的哭声,身体响应着哭声的程度,又压过了阿军……阿宏也是一个病人的儿子,甚至他自己也有病,可为什么他哭起来时,力气大得像屠夫的儿子?“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回家!你们这样对付我,等我长大了,我要杀死你们全村,剥了你们的皮!”阿宏的哭喊如此响亮,就像四个捆绑在一起的人合力而为的,以至于庙内窒黏的黑暗,就像被他的哭喊驱散,天要亮了。然而阿庆的一声断喝,切断了我的这种错觉。
“够了!别哭了!是娘们不是?!”阿庆极力扭动起来,绑住我们的绳子立刻苏醒,勒得人动弹不得,“哭有屁用,再这样哭,把山庙村人惹火了,我找你们算账!……”
我是被雨声吵醒的。当时天已大亮,雨下得正大。山庙里到处漏雨,被阿东搬开的豁口上,雨水更是哗哗地流下来,冲刷着正襟危坐的神像。神像上糊满了黄色的泥巴,泥巴上残留着褪色的标语,或者被撕过的大字报。事实上,这些标语和大字报,仅仅是历史残留的一部分。其余的字写在站立神像两侧的护卫(同样糊满泥巴)和他们身后的墙上,能辨认出来的有“打倒”“斗争”“阶级”等字样。它们如同枯萎的花朵,霉烂在破败的四壁。我猜想这里是“山庙大队”时期开大会的地方,就好比“吴村大队”时期这些字写在大会堂的墙壁上。我还记得父母抱着我去大会堂开大会时的情形,看见有人带着白色高帽跪在台上,台下的人跟着大队干部高呼口号时,年幼的我吓得将尿淋在了身上。
而眼下,在疾风骤雨的包围中,我好像又听到了那些仇恨般的呼喊,我感觉下身湿湿的,转动被缚的手腕一摸裤子,果真湿了。是浅睡时小便失禁了,还是地上流淌的雨水打湿了我?我要站起来,背靠背的阿庆用肘子撞了我,又喋喋不休地骂。原来是他憋不住,尿裤子了。他骂道:“你这个瘟神,痨病鬼……都是因为你放哨时瞎了眼!他们上山时你干什么了?等我松绑了,非挖出你的瞎眼珠不可!”然后又自言自语说:“绳子什么时候才会解开呢?”
这时,庙外突然响起了嘈杂的人声。会不会是我们的父母到来了?我们朝门口张望,看见的是三个戴斗笠穿蓑衣的人进来了。他们的身后跟着许多人。“哈哈哈!吴村佬早该知道,他们也会有今天的下场!哈哈哈哈……”第一个戴斗笠穿蓑衣的人就像傻子一样笑着,笑完了又像傻子一样看看周围的人,周围的人都看着他手中的鞭子。
“大哥,你动手呀!”说话的是那三人中的一个。
“不急,”刚才傻笑的人不笑了,他绕着我们转了一圈,然后把捆绑住我们的绳子解开,重重踢我们一脚,说:“都给我站到墙根去!”我竟然爬不起,昨夜摔下的伤回到了身上。于是鞭子就“啪”地一声真的抽下来了,疼得我一个弹跳蹦起来。庙堂里响起了哄然大笑。
“都站好了,在挨打之前,我要说说清楚,”拿鞭子的人一脸严肃,斟字酌句道,“今天,我们兄弟几个,要轮着鞭笞你们,是因为你们吴村人害死了我弟弟。他叫徐跃进。你们吴村人把他当牛当马,最后害死了他。这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他脑子有问题,可那也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哪……”
人群里有人催促他:“你就少说几句吧。痛痛快快地打!还讲什么道理?当初凑点钱不就赎回来了?”那人把鞭子一挥,反问道:“你这话是替吴村人说的,还是替山庙村人说的?嗯?告诉你,这是在山庙村的地盘上!今天就算吴村人背着钱来赎人,我也照样要这样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非要让事情有个了结!”
他转身,又冲我们吼道:“吴村猴,把衣服都脱了!请裁缝做一套衣服挺贵的,抽烂了可惜。哈哈哈哈……”他一笑起来,又像傻子家的人了。他举起了鞭子,那鞭子很长,先是抽在阿庆的头上,阿庆抱头之时,第二次抽过来,阿宏哎呀一声,鞭子又落在了阿军的身上,接着,又抽在了我的身上。
这一次,我真的把裤子尿湿了。是我自己的尿。当只剩我一个人死死拽住裤子不让脱时,那鞭子就不断地抽向我,热辣辣的尿就一直在流,总也流个不完。以至于第一轮鞭笞停下来时,一种尿失禁的感觉还在延续,它已经随同刺骨的疼痛,抽进火辣辣的鞭痕里。
我听见:“抽抽抽!抽死他!”“活该。偷树贼!竟敢践踏山神……”“‘破四旧’那阵,咱给糊上泥巴是为了保护山神,当时连红卫兵都不敢碰……”可是,又有人说:“害死傻子的人,又不是这几个。”“踩踏神像的人,也不是这几个,早跑了。”“山神就在上面看着哪。他被后人崇敬,是因为仁慈。在他的庙里,这样打孩子……”“还孩子?都快小伙了,还让光屁股,作孽啊!”
山庙村人这样议论着,聚集的人比我们刚抓进来的那个早上还要多。小孩子们又出现了,如同热油中掉进了水珠,兴奋无比。他们看见我们光着身子、抓一把稻草挡在羞处,就万分高兴地欢叫着:“看哪,有一个长毛啦!有一个长毛啦!”
他们指的是阿庆。阿东走后,他就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了。他弓着身子,瑟瑟作抖,双手死死捂住大腿根。终于,在孩子们没完没了的嘲笑下,他哇的一声哭起来:“妈呀,爸呀,你们为什么还不来救我啊?!”
他一哭不可收,引来的是更多人的围观。
之后,傻子一家继续折磨我们。这一回不是鞭笞,是磕头认罪。向傻子磕头认罪。此时,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抱着他儿子的灵牌出现在庙中,就像昨夜那般蓬头散发地哭着,只是不再张牙舞爪地扑过来。她的哭声盖过了雨声和议论。
“儿呀,我可怜的跃进呀,可怜你死前,我一个老太婆,借不到钱赎你回家;你死后,我和你几个哥哥赶到吴村,却没能让吴村人受到惩罚,反被山庙村人笑话……”老女人一边哭,一边将灵牌放在神像前的供桌上。尽管灵牌上没有贴逝者的照片,但是我仿佛又看到那个被吴村人欺凌的傻瓜。他是那么愚笨,丑陋,那么能吃,力气总也使不完,每天被人逼着干活,看着我们傻笑;但是偶尔,也会发疯,两眼直愣愣的,把肩上的担子扔掉,哇哇大叫……
“儿呀,这些年,一想起你喊饿,想起你从小被人欺,娘还哭呀!你活着时,娘没能让你过上一天像人的日子!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娘保护不了你;娘也知道你心里冤……当初,几个哥哥逼你去偷树,被抓住后,他们却不肯出钱去赎你;今天几个哥哥都赶来了,这一回,他们要为你讨回公道……”老女人哭得肝肠寸断,仿佛她也看到了死后的傻瓜,就在我们面前站着。
“娘!今天别说这些丧气事儿!”儿子们把她搀扶到一边,又说,“今天是儿子们为你和跃进报仇的日子哩!你说吧,想怎么处置这几个吴村佬?跃进在天有灵的话,他也看着呢。”可是他们的母亲无精打采,她只是罢了罢手。那几个人就把她丢在一边,转过身,命令我们道:“都跪下!跪到灵牌跟前去磕头!不然……”
——下跪、磕头,对于我们并不陌生,在生活中和电影里都看过。只是在众目睽睽下这么做,感到有些别扭难堪罢了。况且谁会先下跪呢?潜意识里并不想下跪,但是如果有人带头跪了,似乎就会卸下心理上的一副重担。
“怎么还不跪下?还想挨鞭子吗?”
我感到很恐惧,去看阿庆他们,他们低垂脑袋,在傻子的灵牌前站着,都在用余光看旁边的人。于是那个傻子家的老大,骂了一句“他妈的”……鞭子说来就来,咬上来依然那么迅捷,那么锋利。稀里糊涂的,我们四个都跪下了。
“磕头!磕下去!”傻子家的兄弟同时喊道。我们就把头磕下去。虽然有羞耻感,但是并不想反抗,只想着早点儿结束。可能是我磕的不得法,当额头“咚”的一声碰到地面时,突然一阵头晕,两眼也黑了。我感觉就要躺到地上去了,双手无力支撑自己,这时脑袋却突然脱离身体,被一股粗暴的力量抓住,提升到一定高度,又“咚”地落了下去。如此反复三次,我的额头渗出了血。
“哭!都哭起来!大声哭!”傻子家的兄弟气势汹汹地叫着。可是很奇怪,我们都哭不出声来。庙堂内变得鸦雀无声。雨声就显得更大了。而且雨声中夹杂着雷声,远远地传来,就像深山中传来了老虎的低吼。
“怎么回事?不想哭不是?!”傻子家的老大跺着脚,又要动手了,“你们吴村人害死我弟弟,就让你们代表吴村人哭几声都不愿意?他妈的,是不是想以命抵命哪?这就怪不得我啦,我抽死你们!踢死你们!抽死你们!……”他一边用脚踢,一边用鞭子抽,一边呵斥着。
可以说,傻子一家在我们不得不哭出来的哭声中疯掉了。老大打我们的时候,老二老三积极响应也参与其中,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踹我们踢我们,嘴里还振振有词地骂。我们满地打滚,求饶,哇哇哀嚎。就连从来不哭的阿军,这次也哭得很响。他们却不停手……
天又要黑了。我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就如同不知道庙里的人是什么时候渐渐少去的。在又一次昏暗的庙堂内,暂时没有人来折磨我们,但是并没有让人感到放松,而是更加害怕:因为就在下午的时候,阿东被抓回来了。
那时候,傻子一家已经没有“节目”可演,傻子的母亲被山庙村人劝走了。我们找到自己的衣服穿上,发硬的卡其布摩擦一条条隆起的鞭痕,就像在衣服里煨着一根根烧红的木炭。那个与“建业叔”有关的女人(我至今感激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她再一次为我们送来了食物:煮熟的毛芋头。她说上午就来过,看见人多,就又回家了。
“这会儿没人罚你们,快点儿吃吧。建业一定把你们关押的情况告诉你们的爹娘了。就算他没告诉,那个逃走的孩子也该到家了。你们的爹娘今天不来明天准到。难道自己的孩子被抓走,他们放心得下?”见我们没有剥毛芋头狼吞虎咽,她有些奇怪,“吃吧,吃吧,不够我再去煮。分田单干后,粗粮还是够吃的。”
她走后没多久,我们还没有把毛芋头吃光,阿东就被押回来了。押他的人中有在岭背上追捕过我们的人,以及一脸刀疤的壮汉。他们一边一个,揪住阿东的头发迫使其脖子后仰,再往身后反扳住他的手臂,就跟以前推人上台去批斗一样。“老实点!贱骨头,打死你!”一脸刀疤的人喊道,“偷我们村的树,不想交罚款,还想逃走,这还不够,逃走前还带头践踏山神,破坏山庙……告诉你,这要搁在旧社会,按私法制裁,要绞死你!……”
“要绞就赶快绞吧……反正我,死路一条!”尽管阿东强迫做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但是口气仍不屈服。于是,那个一副狰狞面孔的人松开抓住阿东头发的手,窜前一步,一下子掐住了他的脖子。“既然这样,那就让你尝尝绞刑的滋味!”那人使劲地掐阿东的脖子,阿东原本苍白消瘦的脸变得通红,然后又变得乌紫,他一边挣扎一边呼喊“救命”……然而,那个家伙如同鬼魂附体,阿东被他掐得眼睛圆睁,血管爬到了脸上,发不出声了。
情况已经不妙。作为堂弟的我,本该冲上去救他,况且他以前经常帮助我,可我害怕被山庙村人打,怕被同样地掐住喉咙,我矛盾得只剩下哭,一边哭一边战抖……幸好此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人掐住阿东脖子的部位上,有山庙村人担心阿东被掐死了,大声喊道:
“住手!他妈的住手!你难道疯了——”
“我只想让他尝尝绞刑的滋味!”
“你放手……”
掐住阿东喉咙的手被掰开了,顷刻间,奄奄一息的阿东,如同一袋面粉无声地倒在地上。那人朝阿东吐痰,骂道:“去你他妈的×,贼羔子,逃得比狗还快,害得老子在雨中满山地爬!现在怎么样?你不是嘴硬吗?”那人嘬嘬嘴,又扭头说:“包括你们几个,都踮耳听着!明天是交钱赎人的最后期限了。你们的爹娘再不来交罚款,下场将跟他一样!……明天一早,我将带着绳套来,都明白这话的意思了?”
是的,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在这之前,时间对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来说,总是那么宽裕:我们曾经看屠夫杀猪看上半天,捉一只青蛙将它的皮剥下然后放生,或者把两头公牛拉到一块诱使它们打架,空虚得追打正在交配的狗迫其分开……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终止于一座破庙内。相反,那时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长大成人遥遥无期。
尽管母亲也曾批评我“别跟那些坏孩子到处乱跑,有你哭的时候”;尽管我也曾因为吞下耳屎害怕眼睛会瞎掉,因为抠肚脐眼担心肠子会断掉,因为被狗咬担心狂犬病发作然后死掉;以致幻想自己死后究竟会怎么样——是像老师说的腐烂成泥土、回归大自然,还是像母亲说的那样,死后将押往阴曹地府受审判,好人投胎转世、坏人下地狱?我好奇且茫然着。然而,眼下我们面临的,是“把你们一个个勒死在房梁上”。我能感觉到这不是恫吓,不是随随便便的宣泄,而是不断升级的仇恨和惩罚人的快感。这是我活着时的最后时光了。
想到这些,我就再也克制不住了,泪水无声地涌出——因为不论将来像母亲说的那样,学做一个不做恶事的人,还是像老师说的那样,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前提都必需活着——其实我有一个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一名医生,去救助千千万万像我父亲这样看不起病的人。这个理想我深藏心间,从不敢与人言说,因为怕人笑话。此刻,所有理想都失去了意义。
没错,我们已无法逃脱任人宰割的命运。绞死之前,我们的父母不会来了。我猜不出他们不来的原因,是借不到钱还是逃避责任?或者抱着侥幸心理?我不知道该不该恨他们。我只能安慰自己说,我的母亲没有来是因为父亲的病。但是我不会选择逃跑。因为试图逃跑的阿东还昏迷不醒,他的反抗已经让所有人付出了代价。而且我们逃不走,毫无办法。但是我多么不想死啊,还想活着。我伤心得有些喘不上气;伤心得一个人走到一个角落,默默地跪下了。
“山神,山神啊,原谅我们吧,我们知道自己错了,可是……要不是缺钱,我们不会去偷树的。我爸爸得了肺结核,医院治……阿东家也穷,阿东不是坏人,他只是嘴馋。还有阿军家,他爸是哑巴,只知道喝酒打孩子……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山庙村人作恶,你不能不管啊……保佑我们都能活着回到父母身边去吧。”我默默地祈祷并请求山神的原谅,觉得前面罗列的理由不够分量,又依次说出我们每个人的悔恨,尽管这些悔恨许多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当我严肃地罗列出来,首先把我自己感化了。我忍不住向山神承诺,今后我们将如何改过自新,如何去做善事。而后说出自己的理想时,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那是一种悲壮得让人难受的感觉。
可是当我抬起头,虔诚地仰望神像,发现幽暗中的他还是那样冷冷地瞪着我。或许他听不到我的祈祷,也不在乎我的承诺,就像聋子听不到歌唱,瞎子看不到阳光。我垂下头,嘴唇不住地哆嗦,泣不成声。
半夜,我们都睡着了。一遍遍地哭,一遍遍地担忧,一遍遍地难过绝望,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疲惫不堪,似乎就连即将到来的死亡,也不再能够唤起我们对生的渴望。可是变幻莫测的天气,偏偏要唤醒我们,迫使我们去迎接自己的厄运。
轰,轰轰!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可怕的闪电擦亮神像头顶的豁口,也擦亮四周的墙壁,伴随闪电炸响的雷声,震耳欲聋。电闪雷鸣中,我们紧紧地挤靠在一起,似乎这样就能挡住雷击。但是此刻破败的庙宇,犹如一只瑟瑟发抖的母鸡,躲在它的羽翅下并不感到安全。每一次惊雷响起大地震颤,屋顶好像随时会坍塌下来。而从屋顶豁口处流下来的雨水,恍若从越撕越大的伤口处流下的血水,冲刷着神像。神像脱落了泥垢,显露的是一副更加威严、骇人的形象。他虎视眈眈地审视我们,目光逼人。而站立在他两侧的护卫,不仅显得满面怒色,且手拿武器、作缉捕状,仿佛随时会扑将过来似的……
我想,我们是死无疑了。从踏上偷树之路的第一步起,从举起斧头砍下第一斧起,从杉树的伤口流出第一滴乳白色的树脂起,我们就犯下了不能洗脱的罪愆。加上平时生活中,我们还折磨杀死过各种弱小的动物,撒过各种谎,就算这次能逃过山庙村人的追捕,老天也不会就此饶恕犯下罪愆的人。就跟母亲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人在做,天在看”,母亲总是拿打雷告诫我。
我顿时联想到很多天雷惩恶的故事,越发增加了恐惧感。电闪一下我就抖一下,闪电越刺眼动作就越剧烈。我们就这样在惊恐不安、悬心吊胆中挨到天亮。天亮后,雨停了,雷熄了,大地恢复了宁静。此时从狂风暴雨中挣扎出来的庙宇,就像清明节过后湿漉漉的墓地,虽然凌乱,却安静得出奇。又仿佛,那只是一场梦,梦醒时分,一切如旧。以至于上午十点钟左右,当好几家父母赶到山庙时,我们听到脚步声又一次惊恐万分,以为是山庙村人拿着绳索,穷凶极恶地赶来执行绞刑。可是……
山庙村人为什么没有来呢?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几家父母是拿石头将庙门上的铁锁砸开的,庙外既没有看守,也没有其他人。跟随他们涌进来的,是刺眼的光亮,急迫的呼唤,随后是父子母子相见时的哭声、倾诉,和对山庙村人的诅咒。
这是在路上。简直没有比回家的路,更让人感到踏实与幸运——我们没有被绞死:说明我们还将继续活下去,这无疑是这个与偷树有关的故事最美好的结局。然而我有我的心事,因为我的父母没有来。他们怎么了,是父亲病得太重,还是我给母亲丢了脸,她不愿来接我?
我默默地跟在队伍后面,几次想问却没有开口。这时阿东的父亲——他也是我的伯父——一面背着昏沉沉的阿东赶路,一面指着山庙村的方向对我说:“阿昆,你是担心山庙村人追赶来吗?告诉你,半个山庙村被泥石流淹了,你们关在庙里不知道吗?现在山庙村人正忙着救灾呢,所以没人再管罚款的事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难怪昨夜雷声的间隙掺杂着呼喊和哭声,只是听得不够真切。我一时分不清,泥石流的爆发对我们这些被囚禁的偷树贼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我的心忽然有些难受,但是又说不出原因。
“真是奇怪的,昨夜的雨就下在山庙村,那雨一定很大吗?从我们村往这边看,山这边的天空亮得吓人,一个个球状闪电炸响时就跟半边天裂开了,裂缝血红,你说这是怎么搞的,难道真是时候一到,恶有恶报?……”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心情很乱,记不清自己跪在山神面前祈祷时,是否请求过他惩罚山庙村人?……但是我懂得遭遇泥石流是要死人的。现在泥石流虽然消退了,但是朝山庙村眺望,仍能看见倒塌的房屋和冲毁的稻田……但愿没有人淹死,我在心里想。
“走吧,别看啦!”伯父喊我,“竟然有脸对一帮孩子下毒手。我告诉你,山庙村没有一个好东西!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你跟我说说,他们是怎么打阿东的?打他脑袋没有……这账我是不会这么算了的,等下次再抓到他们村的,我非为你和阿东报仇不可!砍断他们的脚,剁下他们的手……”
这些话为什么听着这么熟悉?我仍然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仿佛三天来所遭受的虐待与羞辱,痛苦与绝望,等待与煎熬,霎时重现眼前。我不禁悲从中来,想说出我们遭受惩罚的所有细节。可是我知道这么说,只会引来伯父更多的仇恨,说出更多让我害怕的话。因此我含混地说:“我和阿东……一直等着你们来救的,可你们为什么迟迟不来救呢?再不来,我们就要被山庙村人绞死了……”
伯父愣了一下,把背上的阿东放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阿东醒了,喊了一声“爸”,但是这喊声只有我们能听到,因为声音很小。
“他妈的山庙狗,我说阿东的脖子这么乌紫呢!那些畜生竟然想绞死我儿子——”伯父一脸凶相,又问,“他们是怎么绞阿东的?!”
我见他瞪着我,眼泪就想滚出来。没有滚出来,是因为我之前哭得够多的了,拼命忍着。伯父面露愠色道:“你怎么啦?跟我说说,他们是怎么绞阿东的!”
“我……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越哭越伤心,边哭边喊道,“现在,我只想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有来?没有来!呜呜……”
“唉!你又不是不懂你爹的病,他一听说这事,一晚上咳嗽哮喘……”
“那我妈呢?!”
“陪你爹去治病了!以前不也去镇上治过吗?你这孩子,哭什么?”
可是,我已经控制不住了。
“唉!你爹又没有死,有什么好哭的?”伯父只好反过来安慰我,“当然,这事大人也有错。三天前我们就知道你们被抓了,今天才赶来,一是借不到钱,拖了一天;二是他妈的国梁,不让大伙来,这老流氓!当年他做过‘树干部’,虐待过偷树贼,怕一进山庙村就被人认出来。加上他人品坏,借不到钱。结果他来不成,就不允许别的家长来。好让你们几个给他儿子作伴!而且谁会想到山庙村人,真会对孩子动刑呢?”
“呜……呜呜……”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时的心情,仿佛就此看透了大人们的把戏,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伯父对我失去了耐心,又背起阿东赶路。我一边抽泣,一边紧随其后。
过一会儿爬坡时,我们遇见国梁搀扶着阿庆,挡在山路上。伯父扭过头,装作没看见。国梁就当着众人的面叫喊起来:“路清,怎么样,我说对了吗?只要沉得住气,事情迟早会有转机!要不是我拦着你们,你们几个昨天就赶来,傻乎乎地交了钱,今天这钱跟谁要去?哼,要不要请我喝顿好酒啊?”
伯父没有理他。国梁就指着阿东和我说:“这事,你儿子和你侄子有责任啊。听阿庆说,偷树是你儿子带的头,放哨是你侄子不好好放;抓到庙里后,你儿子还怂恿大家去踩踏神像逃走;你说这么干能不引起山庙村人的公愤吗?我儿子现在满身是伤!回去后,他的医药费和营养费,将由谁来出?”
伯父说:“去你娘的×。让你妈出!”
北京哪家是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白癜风有效治疗转载请注明:http://www.hdnzi.com/wazlyy/1075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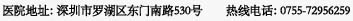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