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品读诗人严敬正午的阳光
正午的阳光
作者:严敬
.12.23第期
那把刀原先躺在路边的草丛里,乌虫认为是他最先发现的,理应归他所有,当他将刀抓在手中的时候,大屁和安良紧盯着他。他把刀装进裤衩的口袋里,若无其事,头也不回地往村外走去。大屁和安良紧跟在他的身后,他们脸上的神情表现出对那把刀的好奇。绕过一条排水沟,林子后面就是菜园地。乌虫在一棵柳树下停住,将刀掏出来放在手掌上细看起来。大屁急忙凑上,大脑壳险些撞到乌虫,闹得叫乌虫别了他一眼。
这是一把剃头刀。没有柄,只有赤裸裸的刀身,刀口失去了往日的锋利,而刀背极厚,显得沉甸甸的。乡下的孩子,无论是谁,都见识过剃头刀,它插在剃头箱的箱盖里,被剃头匠拎着走村串户。乡里第一个剃刀匠是刚望,他的手有些拐,剃头却是好手。儿歌唱道:
刚望剃头,四处难谋,
三刀两剐,就是一个头。
说明他做起活来甚是麻利。但是,乌虫最恨的就是刚望。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剃头,可是刚望隔一段时间就来到他家,叔端坐在屋里,他想溜也溜不成。剃头的时候是最难受的时刻,刚望的小手会在你的头上弄来弄去,特别是冷天,他的凉冰冰的刀子在你的脖颈上咝咝游动。每当此刻,乌虫差不多忍不住要愤怒地大叫。但是他一斜眼,叔正瞪着眼瞧着他。他马上就泄了气。
乌虫推测眼下这把剃头刀应该是刚望用旧的,他多么粗心,把它丢落在路旁。好。往日,他见到剃刀匠展开剃头刀,就忍不住想往他身上吐唾沫,在他自己得到了这把刀子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做一个剃头匠原来还是蛮好的。
乌虫重新将刀装进口袋。走上几步,他就感到有所不便,小有重量的刀身开始企图脱落他的裤衩。为了周全起见,他悄悄地用手提着下滑的裤衩。
“我们去哪?”大屁眯着眼问。
乌虫回看了大屁一眼,阳光刺了他一下,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要到哪去,但是,这个中午总是要被消磨掉的。他又走回了柳荫里,擦起了头上的汗。
“他妈的,真要热死人了。”他骂起街来。
大屁跟着也骂一句,安良瞧着他们俩,如果他不照样来上一句,好像有些不妥,但是,安良他爹不许他说脏话。忽然,安良溜溜的眼睛看见了一只蜻蜓。这只蜻蜓可以救他。
“蜻蜓,那儿有只蜻蜓。”他对乌虫说。
顺着安良的手势看,的确有只蜻蜓。那只蜻蜓青黄色,非常大,是许多出现在夏天里的蜻蜓中最大的一种。人们叫它蜻蜓王,孩子们都想俘虏这样一只蜻蜓。不过,它懂得怎样张嘴咬人。那蜻蜓停在一棵拇指粗、被人拦腰折断的苦楝树上。不论阳光怎样的猛烈,蜻蜓都浑然不觉,看上去,它好像还十分舒服。说不定,它还睡着了。
“我去把它抓来。”安良说,猫下腰就走。
乌虫一把薅住安良,他对大屁说:“你去。”
大屁蹲下身子,走了十几步,接着就四肢贴地,匍匐着靠近蜻蜓。
知了在柳树上拼命地嘶叫。这厮身上似乎也淌起了汗水。整个村庄都落入了正午的酣睡之中。乌虫又看见叔浑身湿淋淋,只穿了一件裤衩躺在堂屋的竹榻上。娘给叔打着扇。最后,娘歪倒一旁,也睡着了。一吃过午饭,乌虫就要溜出屋,如果有一天,乌虫要留在家里,娘反而要把他赶出屋来。乌虫知道叔什么时候出工,就是日头把柴垛的影子斜拉到稻场的那一头的时候。那时,天气并没有稍微凉快一些,路上的泥灰正烫脚。乌虫像贼一样溜回家,竹榻上汪着从叔身上淌下的汗水。黄色的竹榻被叔的汗水浸成了紫红。乌虫顾不得许多了,该轮到他躺着舒坦舒坦了。
大屁就要爬到苦楝树下了,一股混合着泥浆青草的热烘烘的气息使乌虫精神振奋不已。阳光照在晴蜓的薄翼上,发出两片刀刃一般一闪而过的光亮。蜻蜓立在苦楝树上纹丝不动,它要不是睡着了,肯定没有这样的劲头。大屁再爬上两步,只差上那么两步,然后悄悄地伸手,就可大功告成啰。你敢再睡一会儿吗?我们可以打打赌。你敢,好大的胆子。
大屁到了苦楝树下,他要站起身才能捉住蜻蜓。在他直身、伸手的当儿,蜻蜓轻轻一抬身子,飞走了。原来它并没有睡,它没有早早地飞走,是为了逗你们玩的。
蜻蜓在头顶上飞了几圈,又回头去找那棵断苦楝树。意思好像还要歇上一会儿。乌虫重新鼓起了希望,只要它歇上去,就等于给了他们机会。蜻蜓飞来飞去,就是不落下来,乌虫生气了,他发誓,如果逮住了它,就用刀把它切细。
天蓝汪汪的,照得眼睛痛。看不到一丝风。柳树热得昏睡过去。知了仍然长一声短一声地胡乱鸣叫,它们的叫声没有住日的齐整,想必完全是被热成这样。乌虫伸手到口袋里摸那把刀,刀开始还有一丝凉意,叫人不痛快的是,很快刀也热乎乎的,本来刀背是厚厚的,乌虫把它握在手中时,似乎刀口也在渐渐变厚,丝毫没有可以切削的感觉。嘿,是不是这把锈蚀的刀也在打瞌睡呢?
蜻蜓飞得很慢,有一会儿它居然就停在半空中,没有掉下来。这下让乌虫看出来了,蜻蜓肯定也想睡个午觉。不过,悬挂在半空中睡总不如落在苦楝树上睡得踏实,回头它还是要找一个落脚之地。这样,乌虫的念头更坚决了,要是逮住了它,非把它切细不可。
蜻蜓果真又落在苦楝树上。大屁学着猫一样从热烘烘的草上爬过。蜻蜓没有立即飞走,它就是要逗逗孩子们,让他们觉得他们马上就要成功了,让他们流满臭汗的肚皮在热剌剌的青草上多擦上几个来回,然后在关键的当儿,它很轻巧地飞离苦楝树。大屁猛地往上一跃,那一刻他准是想像摘桃子似的从天上摘下这只大蜻蜓。蜻蜓回头望了孩子们一眼,它的眼神充满了耻笑。
“妈的。”乌虫骂道,他弯腰捡了一个土块,照着蜻蜓的影子击打过去。土块没有追上蜻蜓,很不争气地落在刚收完了稻谷的空田里。
往常云山耸立的天空,今天却平展坦荡,毫无趣味。更加使人难受的是,热得要命的天上,像在往地上迸射着蓝色的针芒。到处都闪耀着蓝幽幽的光,连知了的嘶鸣声中也有。
乌虫突然感到不知所措。刚才他的确想拿蜻蜓开刀,但蜻蜓不和他们玩了。现在剩下的就是无法摆脱的空荡荡的、像一块巨石压在身上的炎热的正午。
乌虫瞧瞧大屁,大屁还在为自己的意外失手难为情,他犹犹豫豫,不肯或者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走进柳荫里。
安良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穿了一件横条的海军衫,底下的蓝裤衩也是新的,这件新裤衩在大腿贴缝的地方拉了两道白杠。这身打扮让村里所有的孩子都羡慕得不行。乌虫盯着安良,怎么想都想打安良几个耳光。安良那红润的脸庞,一定非常适合挨揍的。
乌虫的叔经常揍他,他叔就是怎么看都觉得他不顺眼,一不顺眼就拿巴掌打他。叔说他杀没有血、剐没有皮。是的,巴掌打在他脸上他都没有什么感觉了。他寻思,他会不会再也不适合挨揍。他天天等着叔拿出新手段来,但叔弄来弄去就那么两下子。
乌虫还记得他爹的样子。他爹是个能干的庄稼人,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爹到河里打鱼,淹死了。不出两年,他娘就嫁给了他叔。村里人说,他娘早就和他叔相好了,甚至有人说他是他叔的种。乌虫恨村里人的胡说八道,他琢磨他叔心里肯定有数,所以叔揍他还是有许多道理的。娘给他生了一个弟弟,这个弟弟被娘当成了心头肉,对这个弟弟他不知是应该喜欢还是应该讨厌,但有时候他真想掐死他。有一次,他拧了弟弟一把,叫娘看见了,娘劈手就给了他一个栗凿。
“现在,我们去哪?”安良问。
“你想去哪?”乌虫斜了安良一眼。
“去河里划水。”
的确是好主意,开始乌虫就是这样想的,但是这话是由安良说出来的,他就故意不考虑了。他转头对大屁说:“你说去哪里吧。”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大屁说。
“好。你呢?”他又问安良。
“跟你们一起。”
乌虫带头钻进村后菜园地里,另两个也像两头撒欢的小猪崽冲进去。
乌虫马上感到不妙。整个菜园地就像一个大蒸笼令人无法存身。天上如同火焰一般的阳光毫无阻挡地笔直照射下来,而地上的热气更像一团团看不见的火苗围着他们炙烤。没有一棵像样的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片荫凉。所有的禾苗都低垂着叶子,别说像丝瓜、茄子这些有着宽大的叶片的禾苗,就是满身细小叶子的辣椒也扛不住如火的阳光,整个地蜷缩起来。乌虫想,这些东西就跟霜打了一样蔫蔫的,裸着脑壳在菜园地里消磨一个中午,最后怕是也要变得蔫蔫的。乌虫忽然灵机一动,要是钻到丝瓜藤里,或者趴在茄子禾下,肯定会凉快许多。
他首先这样做了。大屁见乌虫蹲在丝瓜藤里,不解其意,还以为他要拉屎。
“好凉快啊。”乌虫说。
大屁望见乌虫满脸大汗,声音里却充满了诱人的快意。他犹豫了一下,就在丝瓜禾旁找到了一蓬豇豆禾钻了进去。
剩下安良。他说:“我呢?”他也想迫不及待地藏起来。乌虫指了指一片茄子禾,而且茄子禾下还有一条厢沟,躺在那里会平平展展。直到安良将他一身的新衣服贴在地上,乌虫才问:“凉快一点吗?”
“啊。”大屁说。
“我的衣衫都汗湿了。”安良说。
乌虫一转头,一条丝瓜正好碰着他的额头,丝瓜刚刚长熟,圆满水嫩,就悬挂在他的眼前。他把丝瓜抓在手里,用力捏着,丝瓜在掌心里渐渐消失,一股绿色的汁液顺着他的手腕流到他的胳膊上。丝瓜的汁液凉凉的,使他心里舒服了好一阵。这样,他认真寻找起来,原来这架丝瓜禾中竞藏了大小十四条丝瓜。他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余下的丝瓜兄弟。他的手臂被染绿了,似乎也成了一条丝瓜。他仍然张着双眼寻找着,最后他问:“安良,你那边有什么?”
“有茄子。”安良说。
“摘两个来。”
安良抱来了两个又白又大的茄子放在他的跟前。茄子圆圆的,光光滑滑,摸着很舒坦。他的脑子忽然闪过一幕令他脸红的情景。他揪住安良的裤衩,问安良:“你说,茄子像什么?”
安良不知乌虫什么意思,没有回答。
“说,茄子像什么?”乌虫又问了一遍。
“像皮球。”
“像皮球?”乌虫说,“不,像你娘的那个奶。”
说完,乌虫就感到脸发热。有一次,他从门缝里看到,他叔掀起他娘的衣襟,娘袒露出两只胀鼓鼓的奶,叔竟然像小孩一般叼住了娘的一只奶头。他从来就没有觉得女人的奶原来这么像两只白茄子。
可是,处理白茄子显然会不简单,首先,它不是真的奶,不能用嘴去叼,此外,茄子充满弹性而少水分,不会整个化成一股水消失掉。
这时,乌虫适时地想到了他的那把刀。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把刀,虽然刀锈蚀得厉害,但它有背有刃,还可称得上是刀,刚才要是捉住那只蜻蜓,用它来切碎蜻蜓一定不会费什么劲。整个中午,他对逃走的蜻蜓都念念不忘。
乌虫把刀看了一遍,抓起一个茄子,好像茄子撞向刀,又好像刀奔向茄子,二者瞬间合二为一,刀完全埋在了茄子的身体里。因为刀轻易满足了他的愿望,使他感到一丝快意,一串汗珠从他头发丛中冒出来,顺着额头往下淌。他顾不得揩一把,认真而充满耐心地去取茄子里的刀。
叔是爹的弟弟,乌虫本来还有点喜欢他的叔。但爹死后,娘嫁给了叔,他就开始不喜欢叔了。他常常用冷眼一声不响地看着叔。娘有时拧他的耳朵,恳求说:“我的老子爷,你不能对你叔有个笑脸吗?你还要靠他养大哩。”乌虫说:“要是我不想长大呢?”娘说:“天哪,你这个小畜生还敢犟嘴。”接着又拧他。
乌虫将茄子剖开,又把茄子削成一片片。在削最后一片的时候,他削到了自己的手指。但他手指居然完好无损。
菜园四周栽满了高架的藤蔓植物,挡住了外面的风。要是有风的话,细长的风也很难穿过密匝匝的叶片。在正午阳光的曝晒下,菜园的禾苗被烤得垂头丧气,似乎奄奄一息了。三个孩子满身是汗,衣衫的颜色变深一些了,紧紧贴在身上。
乌虫的双手暂时歇下来了。他瞟了大屁和安良一眼,两人都像鸡一样张着嘴往外吐热气。他盼望他们中有人发痧,最好是安良。安良的爸是教师,但安良的妈是妖精,有时在傍晚乌虫看见安良妈搀着安良爸走路。安良妈懂得熬绿豆汤给安良喝,即使安良发痧了,也不打紧。
问题是,乌虫自己也感到身上发烫,空气像着了火一样舔他的额头和脸。保不准自己也会发痧的。要是这样,自己躺在床上可能会没有人管。娘那会儿只会替叔打蒲扇去了。乌虫猛然觉得,要在菜园里消磨掉一个中午是不妥当的。一产生这样的想法,乌虫便带头窜出菜园。
菜园的东边是一片稻田,谷子刚刚割过,田还没有耕,已灌上水,正在泡田。稻田尽头是一条土坝,这条半人高的土坝就保护着这片稻田。土坝外面是濯衣港。
眼前是空荡荡的,除了发烫的空气,什么也没有,连一棵遮荫的树也找不到。乌虫犹豫起来,他心里想要不要回到村里去,回到村里,即使不能回家,但坐在塘边的柳荫下,比在这里裸着脑壳让太阳晒不知要强多少倍呢。可是,乌虫清楚,自己要是回到村里,就要想着回家。日影还正得很,离出工早着哩。
乌虫想到回家,就要想到他叔。这是他最不愿想的事。家里有一张桐油漆成的八仙桌,就摆在堂屋里。靠北的上首位置以前总是留给爹坐的,现在被叔坐上了。以前乌虫想坐到桌上吃饭就坐到桌上吃,但现在他不再想坐到桌上去了。乌虫尤其见不得娘对叔的巴结讨好,举例来说,娘不该每碗饭都去给叔盛,惯得他脾气越来越坏。有一次,叔不在桌上,乌虫学着叔把空碗往前一推,意思是让娘也给他盛一碗饭,但娘只顾自己扒饭,硬是装着没看见,弄得乌虫好没面子。他本来要提醒一下娘,刚好叔回来了,他怕叔看出破绽,也顾不上肚子没有填饱,赶紧缩着头溜出了家门。
稻田里只有割剩下的谷茬。谷茬留得很短,泡田的水刚好淹过了谷茬。乌虫绝望地望着空荡荡的稻田,在这片稻田上玩耍恐怕比躲在菜园里糟蹋丝瓜茄子更没有味道。他懒洋洋跳进稻田,水齐到了脚踝,可这水十分地烫脚。他惊得跳了起来。大屁和安良也跳进了稻田,他们都蹦起来了,弄得水珠四溅。
乌虫眼睛一亮,对另外两个孩子说:“我们划水去。”三人一齐蹦跳得更厉害了。
当他们往土坝方向走的时候,他们几乎一齐发现了土坝上站着三只白鹅。村里没有人养鹅,看来是河对岸人家养的。三只白鹅探望了几下,就走下了土坝,进到了稻田。乌虫知道,白鹅是寻谷子来了。一粒粒谷子会把三只白鹅引到稻田中央。这叫乌虫的心里一阵狂喜。他对另外两个说:“知道该怎么办吗?”
“知道。”
他们散开,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弯到白鹅的身后,占据了土坝。他们没有立即发动攻击。三只白鹅发现后路有人,开始它们还不相信三个孩子会对它们抱有恶意,仍然不慌不忙地寻着沉入水底的谷子。但孩子们明显地冲着它们指指点点,它们就不得不留点神了。
乌虫说:“我要宰了它们。”他手里握着那把刀,他明确地感到,他要为这把刀做点什么。他把刀小心翼翼地卷在他裤衩的松紧带里,这样就不会在奔跑中将刀丢失。
三个孩子朝三只白鹅步步紧逼过去。白鹅停止了啄食,望着孩子们高亢地鸣叫一声,十分警惕地注视着他们。和白鹅之间的距离已经相当近了,乌虫觉得没有必要再掩饰他们的用意,就头一个朝白鹅猛扑过去。三只白鹅惊得跳起来,张开翅膀扑腾着朝前飞窜。
追了一会儿,三个孩子一无所获。乌虫马上醒悟到这样弄下去,他们可能一只白鹅也抓不到。他们得重作安排,首先,要有人守住土坝,不让白鹅逃到河里。余下的人一人追一人堵,按这个法子,他们虽然不能把三只白鹅全部抓住,但至少可以抓住一只。抓一只也就够了
安良被指派守在土坝上,他不住吆喝,把想翻过土坝的白鹅吓回去。乌虫和大屁担当起捕鹅的角色。大屁平时跑得比狗还快,现在好像一点也不顶用。他盯住一只白鹅,拼命撵过去,在就要挨着白鹅的时候,他忽然往前一扑,伸出右手,竟捞住了鹅掌。
白鹅的头上有一个肉瘤,圆圆的,很像小孩头上的脓疱,用手去摸,软软的,很是舒服。同时,这疱像一顶帽子,顶在头上,显得气势不凡。乌虫曾经被一只发怒的鹅追赶过,那鹅张嘴就想咬他,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怕鹅。他寻思过,鹅让人害怕,可能就是因为鹅头上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疱。现在,他手中抓住了一只鹅,那曾经令他畏惧的疱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用手去抚摸、摁压这个疱,这个疱松松软软,并且凉悠悠的。他一下子没有了敬畏之心,不住地揉挤,真的舍不得放开手。鹅一直都在摆头,想把自己高傲的头从那只不敬的小手中挣脱出来,但小手像绳子一样缠住了它,使它力不从心。它的两个伙伴已逃到了河里,正在惊恐地呼唤它。
太阳已有点斜了,它的光芒还像金针一样从天上射下来。黄亮亮的稻田里蒸汽袅袅而升。无数只鲜艳的红蜻蜓在稻田的上空盘旋,它们嗅出了蕴藏在稻田里泥浆的灼热的气息。它们就是为了啜饮这种渺不可寻的气味追踪而来的。它们在太阳底下滑过,曝烈的阳光已经熔化了它们的翅膀。有一只红蜻蜓停在空中,它的影子奇妙地落到了乌虫的脸上。乌虫觉得凉了一下,他抬起头,看见那只蜻蜒慢慢地飞走了。蜻蜓侧身的时候,它的翅膀被阳光照亮,发出一道刺眼的红光。
乌虫从裤衩松紧带里解出了刀。这把旧剃头刀也许不是刚望师傅的。在它被人操弄的日子里肯定从许多人脸上滑过。说不定它还失职割破了谁的脸皮。现在它也老了,不中用了,被人扔掉了。但是它被乌虫拾到了,又开始具有了生命。
乌虫早就想好了,鹅头上这个疱虽然柔软阴凉,却不是供给他这样无休止地抚摸的。他们必须和这个俘虏有个了断。
乌虫想好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是有根据的,他听人说过,鹅头上的疱是要害部位,如果遭到击打,鹅就会立即死去。
他让大屁和安良抓住白鹅,自己捏住刀柄,用厚厚的刀背敲鹅头上那个疱。
第一下,鹅大叫了一声,却没有一点会死的样子。乌虫看见刀背的印子留在鹅疱上。他顾不得人们传说的不灵验,马上又敲了第二下。鹅不可思议地痛叫起来。这一下显然有成效得多,鹅疱上刀背印子重叠的地方,凹下去很深一块,破损处有血珠渗出。鹅用一只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乌虫,缩回脖子,张开嘴要啄乌虫。幸好大屁及时腾出一只手,按住了鹅脖子。乌虫一步上前,抓住鹅嘴,接连在鹅头上敲了许多下。鹅的叫声都被闷在喉咙里,偶尔有一声从乌虫的掌心中露出来,显得委屈无助,令人扫兴。乌虫住手了,他拾起鹅头,让大家欣赏他的成绩。
鹅头是一塌糊涂了。原先高耸的鹅疱没有了,那个地方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鹅嘴鹅脸上粘满了血,为了不让血水淹没了它的眼睛,鹅的眼睛还一直在眨着哩。鹅把头伏在浅水里,低声呻唤。
乌虫的结论是,鹅头上的那个疱不是它的要害,他把它砸碎了,鹅也没有死。
“现在怎么办?”大屁问。
“放了它吧,它真可怜。”安良说。
鹅爬起来,东倒西歪地走了。鹅的头上还在流血,它的脸变得狭长尖细。
“走,我们划水去。”乌虫说。
他们到达土坝的时候,鹅也上了坝。鹅扑进水里,朝对岸游去。它的头又昂起来了,它的同伴在那迎接它。
乌虫马上有点后悔,刚才干吗不用刀割了它的脖子?
安良最先脱光了衣服。他的身体又白又胖,乌虫从后面盯着他的脖颈,忽然莫名其妙地觉得安良后颈窝肯定比那只鹅的脖子还要好对付。
乌虫的手颤抖起来。有老半天,乌虫的眼睛都不能从安良的身上移开,他的眼光就在安良的后颈窝上扫来扫去。那把刀不安份地卧在他的手中,一会儿像一块冰,一会儿又像烧红的铁块。
“下水呀。”谁喊了一声。
“哦。”乌虫答应一声,从梦中醒来。他也去脱衣服,他本来已经将刀搁在了草丛上,但他又拾起来,没有再多看一眼,一扬手,扔到河里。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啊,不好了,安良呛水了。”大屁喊起来,跑到岸上。
乌虫抬起头,看到安良正在水里挣扎。他的双手不断地击打出水花。起初,他还认为这是安良同他们闹着玩。乌虫自己就总是装出溺水的样子,引同伴们发笑。
“是不是他的脚抽筋了?”
“不碍事,让他慢慢抽吧。”
过了一会儿,安良不再挣扎了,两个孩子才觉得事情不妙。
“我们要不要救他?”乌虫说。
“当然。”
“那你去。”乌虫又说。
“我不敢。”
“我也不敢。”乌虫从没有这样老实坦白过。“这样吧,我们划拳,谁输了谁去。”
大屁同意了。
乌虫说:“老虎。”
“杠子。”
乌虫又说:“虫子。”
“鸡。”
乌虫瞟瞟大屁:“杠子。”
“虫。你输了,该你去。”大屁说。
乌虫抬头望望空荡荡的河面。他犹豫地说:“安良说不准已淹死了,我们救也没用,还是回村告诉他爸吧。”
两个孩子溜回了村,乌虫先回到家。叔上工去了,但他留下満屋子的汗馊味。乌虫的肚子饿极了,他盛了三碗饭吃,接着,躺在他叔空下来的竹榻上睡着了。
卖猪肉
作者:严敬
.12.23第期
志国是个孤儿,从小能吃苦耐劳,他养了一头猪,当然是指望这头猪能给他攒点钱,其次是淘米水、剩饭剩菜什么的不至于浪费。收工回家,他便忙着打猪草,淘猪食,样样做得细心。这头约克夏猪,说来也争气,经他饲喂,竟特别肯长,捉来不到两个月,已有七、八十斤了。
这头约克夏猪,不仅肯长,看来还是一头聪明的猪。正是夏天,天气热得要命。忽然县里要召集民兵训练,志国是民兵连长,要带队里的民兵到县里报到,这下倒难住了他。不为别的,就为那头约克夏猪。这猪谁给喂呢?
不是觉得这头猪聪明吗?对了,志国想到了一个办法,不妨一试。他找来了两个大脚盆,一只脚盆装糠,一只脚盆装滿水,猪吃完糠,渴了,就喝水,饿了,又去吃糠,不用人喂,猪就自己照顾了自己。假若这头猪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说明这是一头很笨的猪。志国很有把握,这是一头很聪明的猪。这样,他便放心地带着一队民兵到县里去了。一去就是好多天。
转头再说这头猪,它应该算得上是一头聪明的猪,因为开始它就是按志国的愿望那样进餐的,先大口地咽糠,然后大口地喝水。当然也有先喝水后咽糠的。本来,先后搞颠倒也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对头的是,这头猪忽然非常兴奋起来,因为它越来越频繁地与另一个自己会面。起初,它觉得大脚盆里的自己很陌生,看一眼就想赶快避开,后来与那个自己越来越熟悉了,便不由得随便起来。那个自己与自己一模一样,脸上也是兴高采烈的,它试着劝说那见面的同伴出来,它好像答应了,却老是犹豫不决。既然你不肯出来,倒不如我自己进去。这样想的时候,竟慢慢打定了主意。好家伙,这头聪明的猪一个猛子朝大脚盆扎进去,哗啦一声,清凉的水溅出来,溅满猪的一身。一阵凉快,使这头猪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最后,它索性让整个身子浸在水里。兴致最大的时候,它一掀嘴,弄翻了大脚盆,让水流得到处都是。它在被水濡湿的猪圈里快乐地打着滚。这是叫它高兴的事,丝毫也没觉出有什么不妥。
麻烦随后就来了,当这头猪再去咽糠时,却没有水可喝。起初还可忍受,但越往下似乎就无法忍受了。它嗓子眼冒烟,浑身火烧火燎,不住地在猪圈里转圈。不消说,这头聪明的猪最后被渴死了。
志国回家时,猪刚刚死去。他看见一只脚盆里的糠还剩下一半,而另外一只脚盆里的水却一滴也不剩,他对着死猪叹气,惋惜这头聪明的猪因为淘气竟没有按他的设计行事。他没有多想,将猪拖去埋掉。
志国埋猪时被村上的刘老三看见。刘老三琢磨,这猪兴许还没有坏,褪毛开膛,把肉挑到街上,还可以换回几块钱。夜深,他便带着锹,把土里的猪掏出来,烫了,剖了,不消一个时辰的功夫,就将死猪变成了猪肉。
往南,三十里地,过江,就是九江城。肉到街上,不愁卖不出去。猪肉被藏在篮子底层,上面盖着一层辣椒、茄子等新鲜疏菜。子时刚过,刘老三挑着担子摸黑上路了。刘老三合计着,走两个时辰,天刚亮到渡口,然后过江,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
出村,要经过两棵高大的桑树,绿油油的桑树夜晚变成两团黑乎乎的东西。桑树下是一盘石碾,这石碾在星光下泛着模糊的白光。再过去一点,是一个池塘,弯过池塘,就是大路,路两旁是坟地和菜园。这些,刘老三都记得清清楚楚,也是他平日里走惯的路线。夏夜的星星闪闪烁烁,天气凉快无比。刘老三心里的算盘还在噼叭作响,肩上的担子算不得很沉,说起来,他的步伐还称得上轻快。
出村不远,刘老三看见大路旁有个黑影,他好生奇怪,这么晚谁在这里磨蹭。那黑影极轻盈地靠近了,他睁大眼看了看,原来是李二叔。李二叔嘿嘿笑了一下,白牙齿亮得像瓷片,李二叔问:“三侄呀,挑的啥呢?”刘老三怕李二叔知道他偷剐了人家的死猪,就说:“摘了两篮新鲜菜,趁早挑到九江去卖。”“好沉啊,天也黑着哩。”李二叔说。“黑天走路凉快。”“我也喜欢黑天。三侄呀,这些天,我不知老惦记着啥,一人闷得慌,老想找人拉呱拉呱,正好守着了你,搭伴走走。”李二叔挨着刘老三往前走。
“今年夏收咋样?”李二叔说。
“小麦灌浆那会儿,老下连雨,一亩地只收了百多斤麦子。”
“菜籽呢?”
“也不见得好。”
“这么说,上交任务完不成了?”
“分场王书记不是还跑到队里大发了一顿脾气,你不知道?”
“哎呀,我忘了,那年,队长说,要给我家补一分自留地,后来补了没有?”
“补了,这事你也不记得?你家富国还专门买了一包好烟送队长。”
“是呀,好多事我都想不起来,你记性好,帮我想想。”
刘老三以前借过李二叔的锄头用,把人家的锄棍弄断,说好还人家的锄棍,结果一直没还。他自己忘了,李二叔也没有提。这会儿李二叔说这话,刘老三想是不是话里有音。
路面坑洼不平,不断上坡下坡,刘老三觉得夜路真是难走。因为空手的原因,刘老三看见比他年长许多的李二叔走起路来轻盈自如,不过,刘老三没有看见李二叔的脚步在动,而简直是整个身子在往前飘。
想拉呱的李二叔并没有再多说话,两人闷着头一直这样走着。最后,刘老三忍不住了,说:“二叔,我欠你的那根锄棍,秋后一定还给你。”
“啥?”李二叔说。
“锄头棍。我差你一根锄棍。”
“哦,对,我那根锄棍还是栎树的,腰上有个结疤,别还了,我已用不上了。”
远处的村子里开始有公鸡叫唤。刘老三浑身淌汗。李二叔说:“三侄呀,天就要亮了,我得回去。”待刘老三回头,已不见李二叔的身影。刘老三也没多理会,继续高一脚低一脚往前走。
天亮,我们村的一个娘们上菜园摘菜,望见路那边的坟茔里一个人挑着担子正在一堆坟丘上上上下下。她定睛细看,那不正是刘老三么?大清早他在干啥?她亮开嗓子喊起来,这一声喊,惊醒了刘老三。
白癜风可以治吗白癜风治疗哪里最能治好转载请注明:http://www.hdnzi.com/wadzz/643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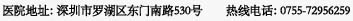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