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美推荐全文蘸火
??文案
我们毕生追逐,毕生灼烧,总想找到什么超脱灰烬的东西,熊熊不灭,获得永恒。
它会战胜刹那又漫长的生命,会打赢羸弱且顽固的本性,会在人间林林总总的平俗动荡中锤炼生长,蓬勃万寿。
直到我们学会相伴,开始相守。
感恩生命,感谢有你。
希望精神永远披荆斩棘,不被疼痛和辛苦所累。
他与那烈火不离不弃。
——仅以我拙劣的文字,献给那只狼狈挣扎,丑陋又可爱的胆小鬼。
你的归宿四季滚烫。
祝岁月悠长,我们从风霜雨雪来归,手捧热望,年少依旧。
钟甯张蔚岚
??冷门儿乖僻美人攻vs不着正调瘪三受
??愿他能拥抱青春的热望,重拾错失
第1章大千世界,冤家路窄
冬季的阴天有时会给人一种“睡懵”的感觉,似乎神智还裹在厚厚的棉被里,尚未跟随眼睛,接触到晦暗的光明。
今儿是个大阴天,瞅老天的面相,八成是有雪要下。空气流动也很不友好,但凡一抻头,东北风几乎能“嗷”一动静,将那半吊二懵的脑瓜抽厥过去。
一辆炫目黑的奥迪Q5吉普,赖在街道上靠边磨蹭。大家伙走出了小裹脚的别扭揍性,车速表盘上的红色针指仅仅宕在十格半。
车里的暖风烘烘造作,吹得驾驶座上的人面皮发烧。
张蔚岚索性伸手,将车载空调掐断了气儿。他闷得难受,又将车窗开了个缝隙。
寒气顺着缝隙溜溜往里钻,拱进张蔚岚的衣领里,黏糊上他的头发丝。
一脑袋凉快逼得他太阳穴猛地一蹦,立时感到一阵头疼,像脑筋塞进麻花机扭崴了一样。
张蔚岚皱了皱眉,赶紧给车窗关了。他又晃荡两下脑袋,好歹缓和了一些。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辆车超了他。这回屁股后撵上来的是一辆香槟金桑塔纳。
桑塔纳车皮璀璨,走位骚包,它掠过奥迪Q5扬长而去,同时不忘短促地“滴”一声喇叭,表达鄙视。——背大号鳖壳的蜗牛崽子都不爬这么慢。
张蔚岚终于给了脚油门,将车速提了提,没让自己的炫黑吉普再搁路面上装大块鸡屎。
前方赶上一个红灯,张蔚岚懒得等,于是打了方向盘右拐。
他将道路走得非常随性,并不是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他此行漫无目的,所以快慢,方向,都无所谓。
张蔚岚稀里糊涂拐进一条街。街角的路牌子在阴天里不显眼,像蒙了灰。上面写着“钟水路”,尾巴底下跟一对小箭头指东西。
张蔚岚打晃看过一眼,扫到两家KTV。这是条商业娱乐街。
半下午了,还有几家店没开门营业。
张蔚岚遛着车轮,兜里的手机响了。
他抄起手机接通:“喂。”
张言欢的声音又细又甜,是典型的小家子丫头:“哥,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月底?或者元旦?”
“找我有事?”张蔚岚不答反问。
“没事......”
张言欢踯躅半晌,知道自己绕不过张蔚岚,只好直说:“你今年能不能回来过年?”
她紧接着半撒娇半央求:“哥,你回来吧,好不好?”
张蔚岚顿了下,没立刻说话,他将车子停了:“小欢,别胡闹了。”
张言欢不乐意:“我没胡闹。”
“就算你不来舅舅这,起码呆在我伸手能够得到的地方。你上个月刚出院,谁能放心你自己......”张言欢说一半自个儿哑巴了。
她放不放心顶屁用?她的混账大哥何时管过别人的心是吊着擎着还是挂着?
张蔚岚果真不管,噎过去一句:“还有什么事?”
“......”张言欢不得不换个茬使劲儿,“那你一定一定注意身体!”
张蔚岚:“......”
张蔚岚实在闹不清楚。他抠良心想,自小便将张言欢用双手捧着养活,结果却不如人意。甭提闺秀,张言欢表皮和里子出入太大,竟实质进化成了个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少教啰嗦货,萝卜根净往他脸上甩。
“一定要按时吃饭你知道吗?一日三餐别不当回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查岗的。你要是再生病,我跟你没完。你听见了没有?没完!”
张蔚岚的头更疼了,被叽喳得很绝望,实在招架不住。
“行了,知道了。”张蔚岚囫囵过两声,没等张言欢再嚎,就挂了电话。
此刻张蔚岚车轮下的土地,是他打小生长的家乡,距离他目前生活工作的城市有些远,有两千多公里的距离。
而所谓的“家乡”,对于张蔚岚,也不过是一个空壳形容罢了。
近些年,张蔚岚回了“家乡”几次。几次,他领教到了“时过境迁”的残忍。
校舍翻新了,老城区的房子扒了重建,年迈的砖瓦全被丢弃。地脉因风霜雨雪的侵蚀产生扭曲,格局颠覆。连同那条鸡零狗碎的旧街道也没了。鸡蛋饼的香味,烤地瓜的热气,糖葫芦彤彤的山楂红,阳光下晶莹剔亮的糖衣……全没了。
他在这里再无亲人,更没有家。
就像老化的皮肤终归会剥落。时间和空间重步更迭,横竖均掩埋在世界的广阔中,死掉,清空,尸骨无存。
虽然一切早已了无踪迹,甚至无法触景融情构成怀念,张蔚岚却还是要回来。尤其近两年,他一有空便会回来,还会独自在这里过年。
张蔚岚会找一家酒店住下,溜达在他不熟悉的,“家乡”的街道上。
张蔚岚明白自己的症结在哪。他总在执着某个虚无缥缈的归宿。或许,他在乞求遇到那座海市蜃楼。
张蔚岚闭了闭眼再睁开,视线产生错觉,四周好一阵天旋地转。车顶似乎刚被他蹬在脚底踩了两秒。
张蔚岚发现,他大概是病了。他的宝贝妹妹真是长了一张活泼可爱的乌鸦碎嘴。
他伸手摸了下自己的头,白费。——如果发烧肯定是全身都烫,自己能摸出根鸟毛?
他又从手边薅起一瓶矿泉水,拧开咕咚了一口。
冰凉无味的液体滑下喉咙,让他舒服了一点。
张蔚岚停车的位置,正右方有一座独栋小楼,墙上刷个花体的“Bar”。
张蔚岚还看到了招牌:“Azure。”
Azure,蔚蓝。
张蔚岚心里倏得动了下。店名和他的名字讨巧,若不是他此刻浑身上下难受得想上吊,他定是要下车,走进去瞧瞧。
但是算了。他一副病躯担不起大任,只能先行打道回酒店。
张蔚岚把矿泉水盖子拧上,然后开车走人,可惜还没等开出去二百米,胃里突然传来一阵绞痛,疼得张蔚岚眼前发黑。
张蔚岚连忙再踩下刹车。他这车今天是开不动了。他没逞能,怕撞车。
张蔚岚捂住自己的倒霉胃,趴在方向盘上倒气儿。
这悲催场面要是让张言欢看见,肯定会数落:“胃不好还灌什么凉水?”
张蔚岚当了几分钟尸体,脑门上的冷汗涔涔往外冒。
他正痛苦,一辆雪白的哈雷大狗忽然一溜风拐过来。摩托上的人穿了件纯白色短款棉服,长腿分跨,正顶风招摇过市。
哈雷正对张蔚岚车门停下。它停下来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张蔚岚的吉普是个黑瞎子,正巧横截在小道出口,挡它前路。
钟甯本想坐在哈雷上,抬头高雅骂爹,但他一扫眼,瞅见驾驶座的那位居然挂在方向盘上,像是一命呜呼,或是命不久矣。
钟甯只好屈尊下地,摘下头盔,绕过去敲对方车窗:“哎,你没事儿吧?醒醒,你还好吗?”
张蔚岚听到有人喊他,勉强擎起一张煞白的脸。然后,他胃里忽作一阵强烈的翻江倒海,剧痛难当。
隔着车窗,张蔚岚好久没能从对面那张脸上撒开眼。
太巧了。海市蜃楼出现了。
……
十分钟后,钟甯坐在奥迪Q5的驾驶座上开车。张蔚岚坐在副驾驶,捂着胃,脑袋死沉,就差给脖子压折。为防断颈,张蔚岚将头靠在车窗上分重,同时翻开眼皮,死眼珠一样盯着钟甯看。
此景万分的戏剧化。找个逗哏的,捏贫腔阴阳怪调哼一段谐谑曲,正好附和。
钟甯是打死也想不到。他今天的糟事,除了睡到中午起床,头昏脑胀,上厕所又搁厕所门框上磕了脚丫子以外,还能在抄小路去自家酒吧的途中,捡到一个半死不活的故人。
提起张蔚岚,曾经的某一时段,他是离钟甯最近的人。他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在一个泥坑中打架,在一间教室里懂事……他们跺彼此痛脚,挖对方心窝,更有太多大不韪,交换过情窦初开,分享过欢喜悲伤,互相泼洒满脸的滔天怒恨……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最亲密,分开的时候最决裂。
钟甯打心眼里认为,他与张蔚岚,爱恨皆曾歇斯底里,结局该是“老死不相往来”,“魂飞魄散于江湖”。
奈何岁月磨刀,手起刀落,抽刀难断水。江湖上风云多变,他们还没等老死,就又相见了。
——大千世界,冤家路窄。
“他一点也没变。”钟甯看到人的一瞬间,心肝脾肺好一顿南簸北颠,硌楞出了第一个想法。
一秒后他又想:“还是变了。”
“你又是胃疼又是发烧,医院真的没问题吗?”钟甯的目光直视前方,太直视了多少有些僵硬。
张蔚岚愣了一会儿才说:“没事,不严重,现在已经好多了。你送我回酒店就行,我有药。”
张蔚岚:“没耽误你什么事吧?你摩托车都停路边了。”
“没关系。我今天也就是出来随便逛逛,没什么正经事,不耽误。”钟甯说。
他这么说也不算蒙骗。Azure有徐怀那个靠谱的帮忙打理,钟甯作为老板,当惯甩手掌柜,浑不是玩意,平素只会打酱油,白坑店里的酒喝,的确不算正经。
不正经的转念寻思:“张蔚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怎么就回来了?他当年不是说“一辈子都不回来”吗?
不过张蔚岚住酒店,那应该是刚回来还没稳当落脚?或者有什么原因暂时回来几天?
钟甯:“你就住酒店?”
张蔚岚的目光动了下,“嗯”了一声。
钟甯:“......”
钟甯发现自己再问不下去。时间是个毁灭者,甚至让他找不到一种熟稔自然的语气,用来面对一位故人。
钟甯终于瞥去一眼余光,瞄到张蔚岚在皱眉。
这人病成这德行,还敢独自拽着吉普上街。
不过张蔚岚以前就这样。他两极分化得很,轻重不挨,小命还没扽裂算是奇迹。他有谱没心,要么稳稳当当,就算头上摞十个碗碟站高脚凳,都能像耍杂技一样纹丝不动。但若是他捅了篓子,定要将无底洞戳穿,一屁股栽十八层地狱坐实惠。
——看来还是没变。
钟甯一路上不走字儿,张蔚岚全身难受,也没提话茬。阴森森的大白天,连鬼都不敢穿进车嗝屁。
直到到了酒店门口,也没人多崩出一个字来。
“那我走了。”钟甯和张蔚岚对视时移开了目光,跟火烧眼球似的。
张蔚岚胃疼得一撕二挦,他想:“你还那么恨我吗?连看我一眼都不稀罕。”
张蔚岚终于说了句重逢时该说的客套话:“留个电话吧。今天多亏你,好久不见了,下次请你吃饭。”
“......好。”钟甯脸上贴着“大人”的“客气”,掏出手机,和张蔚岚交换了联系方式。
存好电话,钟甯微微皱眉说:“你病了多休息,医院。快进去吧。”
他差点问张蔚岚:“谁照顾你?”
但这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钟甯顿了顿,转身走人,甚至没跟后面那句“下次再联系”。
张蔚岚胃里又狠抽,他脸色更白,疼弯了腰。今天的空气特别冷,周遭如同一口煎熬大冰块的零度铁锅。
“我错了。我再也不走了。”张蔚岚心说,“你转头让我再看看。求你。就多看一眼,我去死也知足。”
第一卷?热钢
第2章钟家有些玄乎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了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哎,进呀进不来。”
钟甯少年时代最头疼的事,就是被自己外婆“绑架”,听她唱曲儿。
“外婆”这个称呼搁他们这不常用,整个三趟街也就钟甯一张嘴从早到黑地喊,别家的小孩都叫“姥姥”。
是严卉婉本人不让叫“姥姥”的。她嫌弃,非说“姥姥姥姥老老死了”,让外孙改个说法。
严卉婉是三趟街道最时髦的老太太。说“时髦”算褒义派,还有一部分贬义派,经常红着眼背地戳脊梁骨,骂她“老嘚瑟精”。
她今年正值六六大寿,喜好将一头斑白的短发烫出蓬松大卷,左侧鬓边习惯夹戴各式各样的发卡,有带水钻的,带珍珠的,有琉璃的,有树脂的……多姿多彩,什么天鹅大蝴蝶,繁花小月牙……梳妆台专门倒个大抽屉放发卡,轮换着戴一个月不会重样。
上身的衣服也偏爱新鲜色,不是红橙黄绿印牡丹,很难能入老太太的眼。
老太太手也巧,转得了手绢,敲得响腰鼓,水袖一甩,引领街区老年舞蹈队奔夕阳,出尽了风头。
严卉婉年轻的时候丈夫就病死,她如今能这般潇洒,靠的是有个出挑的闺女。
她闺女叫钟姵,钟甯亲妈。
钟姵不是善茬,某种程度上她是个恶茬。
那个年代人都迷信,算命打卦的说钟姵命硬,身上带煞,甚至她刚会跑,就被指责克死了亲爹。可严卉婉不管那套,照样一把屎一把尿将钟姵拉扯大。
严卉婉当钟姵是手心肉,怕她委屈,又撑着不肯改嫁。
可惜孤女寡母总归坎坷。
钟姵二十三的时候怀了钟甯,没结婚,孩子是被强奸犯强出来的。
钟姵那段时间肚子里揣货,成天想死。严卉婉抹着眼泪拎她去妇科堕胎。
那天医院,又突然诈尸一样,一溜烟跑了出去。
于是钟甯就没死成。
钟姵对严卉婉说:“这孩子我要了,不管他是男是女,都叫钟甯。”
——“甯”,说是有宁死不屈的意思。
大概是上苍垂怜,红鸾星天降,医院就去买彩票,改明儿竟中了二等奖。钟家于是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钟甯生下来不久,有消息说钟甯的强奸犯亲爹死了。就在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躲到化工厂,掉污水池里呛死了。
钟姵这女人心肝长得不对称,竟在自己儿子面前大笑:“这畜生死的好!普天同庆!”
钟甯遗传钟姵的骨血,当时他屁大的孩子,“妈”都哼不清楚,居然能歪头咧嘴,嘿嘿直乐。
至此,外人都觉得钟家有些玄乎。
钟姵领了女强人的人设,并没坐吃山空。她出去抛头露面,仗着长相娇美,能力出众,结识了不少大老板,做起了物流生意。没过几年,钟家越来越富裕,成了三趟街实至名归的有钱人。
人红是非多,嚼舌根的也不少。街头巷尾的七姑八姨,明面摆出一副“笑贫不笑娼”的姿态捅刀,暗地还放枪,直说钟姵是个荡/妇。
严卉婉听了以后,成夜在家掉眼泪,钟姵一声冷哼,询问到是谁惹她妈哭,第二天拎着一把菜刀,就最近的一家踹门,给人家里一通砸。
砸完还甩一把臭钱作赔偿,又说:“‘荡’我认了,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投胎这张脸,春风对着我就吹,跟你们这些冻死在脏土堆里的窝瓜不一样。但是‘妇’,我告诉你,老娘就算再生八个儿子,依然是少女。管好你们的狗嘴,再惹我妈哭,我掀了你家房顶。”
后来再没什么人能乱呲牙。
可见,钟家这母女俩,祖上得是掘人坟墓的土匪。
现下,钟甯正蹲在严卉婉对面一把红木椅子上当蛤蟆,被外婆转脱的手绢盖住脸,闹了个红盖头。
“外婆唱得好!”钟甯一巴掌揍响红木把手,回馈亲外婆一出拍案叫绝,“真的太好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钟甯薅下脸上的红手绢,朝严卉婉竖起大拇指:“外婆,你是人间富贵花。”
钟甯是分毫没觉得,外婆给白毛女配着扭了遍东北“一人转”有什么不妥,笑嘻嘻地将红手绢递给了严卉婉。
老太太被钟甯的小嘴哄得眉开眼笑:“就你会说话。”
“哪儿呀。”钟甯一高从椅子上蹦下来,蛤蟆落地,“外婆唱的就是好。”
他们钟家男人缘不好,钟甯一枝独秀,自然是宝贵。钟少爷从扒蛋壳起,几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也讨人喜欢,恃宠而骄的同时,油腔滑调的功夫修炼得炉火纯青。
钟甯抱住严卉婉一只胳膊赖塞:“外婆,我晚上想吃地三鲜,还有炸鸡腿。”
“好,外婆给你做。”严卉婉拍了拍宝贝外孙的手。
钟甯赶快捏两下严卉婉的肩膀:“外婆真好。”
屋内正祖慈孙孝,院里忽然传来一串大响,劈里啪啦,像是什么东西接二连三摔了出来,又掺和进嗷嗷的狗吠。
钟甯:“是大朵子在叫!”
“这是怎么了?”严卉婉皱上眉头,拍了一下钟甯后背,“你快去看看,是不是东头又出幺蛾子了。”
“哦。”钟甯接旨,撒蹄子跑出去。
钟甯家独家大院,四方四正。院里两间平屋,立地而起。坐北朝南的一间大,自家住。
东侧的那间小,出租,给了吕箐箐一家。
吕箐箐不是别人,是钟姵闺蜜。两人从扎羊角辫的时候就一起念书,感情很好。
可怜吕箐箐不开眼,十八岁跟了张志强。
张志强是穷光蛋,家里还剩个光棍老爹当破烂拖油瓶。吕箐箐却愿意对抗父母,所向披靡,单瞅他一张俊脸吃饭。两人年轻意气,情比金坚,囫囵过几年登了记,生下一个儿子。
早些年吕箐箐爹妈过世,他们没地方去,钟姵这小屋算是救济他们,每个月崩星意思点租金就算完。钟姵又帮张志强介绍了些海上的活儿,能支持他们一家四口生活。
吕箐箐过意不去,经常给严卉婉捏肩捶腿,扫地做饭,挣了老太太欢心,又帮钟姵尽孝。
所以单挑吕箐箐这个人,和钟甯家还是有不少情意在。
于是钟甯没怠慢,他几个箭步冲出去,临门口脚下打秃噜,搁瓷砖上滑了半米漂移。
他一推门,正巧看见一个小马扎起飞,落地“咣当”“咣当”,被砸颠了个儿。
“你滚!丧天良的王八蛋,你出门就得被车压死,你死了我一滴眼泪都不掉。”吕箐箐扯着尖嗓门谇。
“你少又摔又拎的,你作这一套给谁看?你看看你现在的德行!”张志强紧接着怼上。
钟甯看见,吕箐箐后退着,两步从门口绊了出来,不到半秒张志强也撵出来,伸手戳吕箐箐鼻子:“你这个泼妇。”
看来吕箐箐是被张志强推出来的。
“我泼妇?我呸!”吕箐箐喷张志强一脸唾沫,“你怎么不说你在外头不做人事?养那么个婊/子精,还生了个小婊/子。”
张志强一抹脸,急了,刻薄地骂:“你还不如婊/子,你看看你肚子上那圈肉,坐下两个褶子,站起来颠三下,丑死了!”
“我丑?我没给你生儿子之前还不是一尺九的小腰?你这个没良心的牲口,我跟你拼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吕箐箐边骂边去捡一旁的小马扎,对着张志强抡。她脚丫上蹬了双拖鞋,踩在一地杂碎上,左脚脚后跟不知被什么割得,正滋滋冒血。
钟甯没有太目瞪口呆,张家两口子经常闹得鸡飞狗跳,不过今儿个这架势着实剧烈了些。
就在钟甯琢磨要不要上去拉一把,拉谁更有胜算的时候,院门口突然“刺拉”一声刹车。
一辆大货车停在门口,驾驶座的门打开,下来的竟是个娇小漂亮的女人。——是钟姵。
钟姵脱下一双恨天高,左右手各一只鞋,打眼一看,她便是个从滚滚红尘里摘出来的光脚美仙,大步生风。
钟姵张开一双烈焰红唇:“张志强,你个龟孙养的孬种,在谁家院子里撒野?你动箐箐一下试试,老娘叫你满头都是窟窿!”
她话音落下,挤开吕箐箐,立时举起手,左右开弓,将细长的鞋跟往张志强头上捶。
张志强八分躲,一分忍,剩下一分推搡着还手,嘴皮骂骂咧咧,听不清是什么浑话。
吕箐箐眼瞅替她出头的回来了,一屁股坐地上,手掌拍地哭嚎:“我怎么瞎了眼跟了你这么个王八蛋!”
钟甯实在不敢愣着继续看戏。他嗷一声跑进战场:“妈!”
钟甯一把抱住钟姵,将人往后拖:“妈,妈,别打了。”
“你滚蛋,不关你事。”亲妈并不搭理他,慌乱中没注意,胳膊肘拐了下钟甯的脑袋。
眼见闹剧愈演愈烈,就要无法收场,严卉婉老太太忽然出现在门口,老泰山一样,稳稳当当喊了一声:“再打我报警了,都滚出去,去警察局打吧。”
空气好像凝固了一秒,气氛陡降,钟甯终于将亲妈拽后几步。
“钟姵,把你的鞋穿上。什么德行。”严卉婉教训完,又去看地上的吕箐箐,“箐箐别在地上坐了,来进屋里。”
老太太说完就扭头进屋,谁都不稀罕再搭理。
钟姵瞪了张志强一眼,挣脱钟甯,扶起眼泪八叉的吕箐箐进了自己家门。
张志强和钟甯脸对脸站了一会儿。张志强朝地上啐了口浓厚的唾沫,转身走出院门。
钟甯瞪着张志强的背影看了两秒,朝他比了个中指。
去他妈的张志强,他就是个张弱智。
这场“腥风血雨”全怪这个弱智。
张志强表面吭吭哧哧,实际是柜里锁的偷腥货,早在外头找了个女人。也不知他兜里没几个子儿是怎么勾搭的人,贱胚子果真埋哪处臭水沟都能发/骚,挑都不挑。
更该死的是,他还跟那女人生了个野丫头。
闹成这样是因为纸包不住火,终于暴露了。
这些是钟甯后来听严卉婉唉声叹气叹出来的。她觉得吕箐箐难,再琢磨自家情形,最后归纳出一句:“女人啊,命真苦。”
这全是后话了。
当下一场闹剧结束,钟甯杵在东屋门口站了一会儿,揉了揉被亲妈一胳膊肘拐懵的脑袋,突然回过神:“狗怎么不叫唤了?”
他大喊了一声:“大朵子!”
钟甯喊完不到五秒,对眼的门里拱出来一只土黄色大狗。
这狗分不清是哪串杂种,站起来到钟甯膝盖高,是当年严卉婉逛早市,十五块钱牵回来的,进门时还是个跛蹄崽子。
它虽然血统不净,但胜在腰条顺当,脸盘清秀,尤其眼球,跟黑珍珠似的。
这狗一双耳朵特别大,像两个蒲扇,偶尔动两下,又像大花瓣。钟甯给它起名叫大朵子。
“大朵子,你是谁家狗?舔谁家饭碗?往别人家穷钻什么劲儿?”钟甯没好气儿地批评,“你这头弄得什么?真恶心。”
大朵子呜呜嘤嘤特别委屈,一脸的黏糊糊。钟甯蹲下来,皱眉屏气瞅了瞅,判断是鸡蛋液。
估摸是张家两口子打架,大朵子去裹乱,被迎头赏了两颗笨鸡蛋。
钟甯啧一声,正嫌弃,门口又出来了个人。
钟甯抬头看,是张蔚岚。张志强和吕箐箐的儿子。
刚才亲爹亲妈好悬没打成筛子,这亲儿窝哪去逍遥了?居然现在才现身。
张蔚岚手里拿着一条湿毛巾,一个哑屁都没吭,蹲下来薅住大朵子后脑勺上的毛,给它擦了一把脸。
文档点击左下方
文档点击左下方
文档点击左下方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hdnzi.com/wazz/1394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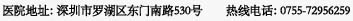
当前时间:
